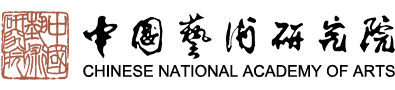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传统
时间:2023-10-12 来源:中国艺术研究院官方网站 作者:田青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是“一院两所”,也叫“三大所”:中国戏曲研究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民族美术研究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就是毛主席为三大所之一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提写的。三大所是真正有传统的,它由一代又一代的人积累起来,又凝聚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传统。回顾七十余年院史,我认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有三大传统。
一、爱国主义的传统
一个人没有爱国主义成不了大学者。爱国主义不单是一个学者的基础,也是任何人都应该有的基础品质。
梅兰芳是中国戏曲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20世纪40年代日军侵华,中华民族陷入巨大的苦难。梅兰芳坚决不给日本人和汉奸唱戏,蓄须明志,整整八年息影舞台,一度要靠卖房度日。他还曾经为了拒绝给日本人演出注射伤寒针,故意让自己发起高烧,体现出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忠贞肝胆和爱国主义情怀。由此我想起唐朝梨园弹琵琶的乐工雷海青。安史之乱时,安禄山攻占长安,很多文臣武将都被俘投降。安禄山在凝碧池大宴群臣,昔日的梨园乐工被迫奏乐。而雷海青当着安禄山和投降的文臣武将的面,愤然将手中的琵琶摔碎在地,向着唐明皇西去的方向放声痛哭,坚决不给安禄山演奏,最后被叛军在戏马殿前车裂而死。
还有副院长程砚秋,四大名旦之一,当时日本人要求北平梨园公益会出面组织京剧界义务表演,筹钱为日军捐飞机。威逼之下,很多人不敢不唱。但程砚秋严词拒绝:“我不能为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能让大家受牵连。献机义务戏的事,我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请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的麻烦,我自己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重重压力下,程砚秋决定息演、退出舞台,到北京青龙桥务农生活,当了农民。养鸡、种地、写字、画画、读书,就是不给日本人唱戏。
中国艺术研究院还有一些艺术家,比如张庚、王朝闻、李元庆等,都是解放区来的,都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正式代表,曾亲耳聆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该被称为革命艺术家或者红色艺术家、理论家。张庚是戏曲研究所的所长,早年在上海搞话剧,后来研究传统戏剧,40年代初来到延安,是延安鲁艺的戏剧系主任,对建国之后的戏剧研究有开拓之功。中国艺术研究院三大所都有两个奠基石,叫作“一史一论”。“史”是纵向的,“论”是横向的或者深入的。张庚开创了“前海学派”,奠定了戏剧研究的“一史一论”。他在三四十年代就写过《论话剧民族化和旧剧现代化》,讲传统戏剧的现代化,能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提出这样的思想,这些前辈们的眼光令人惊叹。
王朝闻是中国的第一代雕塑家、美学家,他是我们美术研究所所长,最早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封面中间就是王朝闻创作的毛主席侧面像。
李元庆是音乐研究所第一任领导,当时在延安是大提琴首席,《白毛女》的首演就是李元庆拉大提琴伴奏的。当时请他做所长,他说:“我当书记、副所长,让杨荫浏当所长比我更好。”就这种胸襟,现在谁能做到?杨荫浏是一个大学者,没有杨荫浏就发现不了瞎子阿炳,也就没有《二泉映月》,也不会有智化寺京音乐、河北吹歌和十番锣鼓。后来他就专心做他的学问,音研所的事务性工作都是李元庆在做。李元庆是共产党员,从解放区来延安鲁艺的,他为什么甘居副所长?我想是为了工作需要,他觉得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要这些名利。李元庆做了很多工作,音乐研究所当年做的一系列重要的音乐普查都是他安排的。
关于杨荫浏的爱国主义我想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杨先生写《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年轻时,他曾经听一个美国学者讲《世界音乐史》,从头讲到尾没有一个字提中国。杨先生说:“我想不通,中国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有这么多的音乐,世界音乐史里一个字儿都没有。”所以他决心开始写《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他用英文写中国古代音乐史,目的就是要为中国人争气。第二个例子是杨先生为《满江红》填词。抗日战争时期,正是杨先生饱含深情地将岳飞《满江红》的词句填到了元代萨都剌《金陵怀古》的古曲中,随后,这首《满江红》在那个民族危亡的特殊时刻迅速传遍了全中国。
再看缪天瑞院长,缪先生一辈子慈祥、和蔼,他是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启蒙者。他介绍了交响乐、奏鸣曲、贝多芬、莫扎特……他还研究律学,这门在西方不能被称为专门学科的律学,被他做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1949年,大陆解放,身为第一任台湾交响乐团副团长的缪天瑞,放弃一切,带着全家老小,雇了一艘小渔船,冒着生命危险,西渡回到大陆,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为国效力。
吴晓邦,舞蹈所的所长,也是爱国主义者。他没去过解放区,和张庚、王朝闻不同,他自己单打独斗,在上海创办舞蹈教育机构和舞团。当年《义勇军进行曲》刚一问世,吴晓邦就据此编创了男子独舞,并亲自表演。他还编舞了贺绿汀的《游击队队歌》,把当时的抗日歌曲第一时间改编成舞蹈形式。20世纪50年代初,他到山东曲阜摄录了孔庙祭孔乐舞的珍贵纪录片,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库里的重要资料。正是这样一批我党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奠基者,也是建国之后整个新中国艺术事业的开创者。
什么是爱国主义?我认为可以用“身土不二”四个字来概括。“身”就是身体,“土”就是脚下这个土地,“身土不二”就是你的身体和你脚下的这片土地彼此分不开。那年我去韩国访问,正值金融危机,韩国、日本、香港深受影响。有一天我正在汉城(首尔)街头遛弯儿,突然看见两栋楼中间的树旁竖着一个杆子,上面挂着一个长长的白布条,上写四个大字:“身土不二”。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当时韩国老百姓会把自己家里存的金银首饰拿出来支持国家货币,跟国家共渡难关。这四个字,给我印象太深了!“身土不二”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既不是那些空泛的道理,也不需要理由,你爱国和爱你妈妈一样啊,需要理由吗?需要什么理论支持吗?应该是你与生俱来的、完全应该有的品质。
二、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传统
我们做学问为的是什么?这是灵魂之问。为了拿个文凭,找份工作?这不是做学问的理由。做学问的目的一定是追求真理。
一件事情,将它剖成两半、认清本质的过程,叫作“判”。这是做学问最基本的方法。科学求真,宗教求善,艺术求美。真、善、美是有分工的。不管你学的是艺术学、音乐学,还是舞蹈学,后边只要加一个“学”字,就构成了学问、学科、科学。科学就是要求真。做学问的动力、目的是追求真理,方法是实事求是,但实事求是并不容易。
1982年,我研究生刚入学,美术研究所所长王朝闻给我们上课,当时我们真有幸,刚才我说的这些人,除了梅兰芳、程砚秋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其他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我们当时学习的《美学概论》教材主编就是王朝闻。很快,我在看书时发现了一个问题,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情感成为音乐的内容,必须不是纯粹个人的、偶然的,而是带有社会普遍性的、可引起共鸣的,同时又必须与一定的音响变化相适应,符合乐声的规律性。”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艺术家、艺术作品,绝大部分是表现个人感情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表现的都是杜甫个人的感情。但是,他的个人感情引起了更多人的共鸣,他与人民大众的感情是一致的。所以我认为反映个人感情的作品不能成为优秀艺术作品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一是因为年轻气盛,一是因为对真理的追求,我就冒昧地给王朝闻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时我只是个刚刚入学的新生,没想到王先生立刻给我写了回信,他说:“田青同志,你的信我收到了,虽然我手头现在没拿着这本书,但是我只看你引用的这句话,我就认为你是对的,我同意你。而且说如果所有的读者都像你这样,提出问题来,以后我们这本书会越改越好。”王朝闻先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这样的虚怀若谷!要知道,我的这句话怀疑人民大众而提倡个人感情,这在文革时不是小问题。但是,王先生不因为我是一个无名小卒而置之不理,他虽是大家,却亲笔给我回信,并肯定我的“实事求是”,这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也更加坚信实事求是是追求真理的必要条件。
三、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可以从杨荫浏和阿炳的往事说起。杨先生和阿炳都是无锡人,阿炳比杨先生年长十几岁。他们早就认识,杨先生还跟阿炳学过乐器和十番。没有阿炳就没有《二泉映月》,杨先生作为音乐学家,他碰到了阿炳的音乐,把它记录下来,整理成谱子,推荐到中央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送,让全世界知道了瞎子阿炳,知道了中国的《二泉映月》,尽到了一个音乐学家能做的最大努力,将理论研究和音乐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另外,杨先生还研究被称为绝学的“律学”,但他并不局限于单纯的理论研究,更加关注音乐的实践。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设计制作了一把尺子,还用这把尺子教给乐器铺的师傅们怎样给笛子开孔、怎样给琵琶贴品,音才是准的。他在探索如何把自己的理论所得用来指导音乐实践,一直在进行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努力。
还有新疆十二木卡姆和万桐书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初,原新疆省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维吾尔族珍贵的古典大曲“十二木卡姆”濒临消亡的情况,周总理高度重视,指示文化部组织专员赴新疆完成抢救工作。最终,文化部选派28岁的万桐书前往新疆。路途艰难,万桐书夫妇带着一岁多的女儿,三月份动身,五月份才辗转来到新疆。在新疆他们见到了70多岁的吐尔地阿洪,他是当时新疆唯一可以将长达19个小时的十二木卡姆完整演唱下来的人。当时城里只有一家小发电厂,一天供电1个小时,电压极为不稳,万桐书等人克服重重困难,历时两个多月,录制了24盘钢丝录音带。录音之后的记谱和翻译工作更加困难,直到1960年以五线谱记录的《新疆十二木卡姆》终于正式出版,从此,新疆十二木卡姆改变了过去口耳相传的单一传承方式,开始有了文本形式的留传。可以说,当年如果没有万桐书他们去新疆,十二木卡姆就不会被记录下来。这个工作的完成也为2005年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成功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奠定了基础。我国的十二木卡姆完整度是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这就是音乐工作者万桐书的贡献。
还有一位音乐工作者周吉,在万桐书之后继续到新疆研究木卡姆,他也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申报教科文非遗的申报书起草者。木卡姆地域性很强,总的叫木卡姆,细分有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伊犁木卡姆,还有十二木卡姆。现在像吐尔地阿洪这样熟悉完整十二套木卡姆大曲,而且都能唱的,已经没有了。即便一个维吾尔族艺术家也只熟悉一个地区的木卡姆,为什么周吉这个汉族学者能够整理研究它,能够撰写《木卡姆》?归根结底,是因为有大量的田野工作为基础,因为理论联系实际,这才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传承到这份文化遗产。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曾经积累了让全世界瞩目的珍贵音响档案——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这是一份长达7000多个小时、涵盖我国50多个民族或文化群体的传统音乐田野录音资料。音研所建所70年,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工作者,不辞辛苦奔赴新疆、贵州、广西、东北等全国各地进行音乐田野工作。其中,有几次影响深远的大型音乐普查。一是杨荫浏亲自带队的《湖南音乐普查报告》,几个月的时间,跑遍湖南20多个县,从民歌、民间音乐到宗教音乐,全都采录完整,影响很大,为我们后来非遗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也积累了如何采风、录音、记谱的经验。另一次影响较大的音乐普查是当时音乐研究所做的《河曲民歌采访专集》。找民歌只有去穷乡僻壤,因为经济不发达,民歌才能保留下来。穷乡僻壤和生活困苦造成物质的极大贫乏,爱情和精神生活成为唯一化解痛苦的途径。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婆姨、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困庄稼汉,才会把他一生中只有这一次的铭心刻骨的爱情化成上下句的民歌流传至今。我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以后,几乎所有乐谱都送人了,但有一本《河曲民歌采访专集》乐谱,我舍不得送。因为我一翻开,一试唱,就掉眼泪,太好了!这本乐谱就是当时音研所的工作人员,十几个人坐着驴车马车,驮着自己的行李到河曲,和农民住在一起,历经几个月时间记录下来的1500多首民歌。今天脍炙人口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兰花花》《走西口》《三十里铺》等都是那个时候记录下来的,太珍贵了。1997年,这份7000个小时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被全世界看到,举世震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珍贵档案。现在这个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已经上线了,这是我们音乐研究所和艺术与文献馆一起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把7000个小时录音免费提供给全世界,里面有多少辛苦?有多少人的劳动?
研究院还有一个宝库是70年来一代代音乐人收集的乐器。一共收集了1000多件乐器,仅古琴就有92张。从唐代的枯木龙吟一直到民国琴,是全国馆藏古琴数量最多的。五六年前我做“让古琴醒来”的课题,把唐代的“枯木龙吟”拿出来,让琴家演奏,让大家欣赏,让枯木在盛世发出龙吟。因为乐器和其他文物不一样,乐器是有灵魂的,有灵性的。长时间不演奏,哪怕是恒温恒湿的保存,对它也是伤害,乐器是越弹越好。世界上也有这样的经验,比如中世纪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现在存世的大概有100多把,收藏在民间、博物馆、基金会等处。其中很多把这样的名琴,都委托小提琴家来使用。甚至有的基金会还举办一些比赛,如青年小提琴比赛,冠军奖品就是一把斯特拉迪瓦里让你演奏一年。我们国家文物局也发了通知,但响应者寥寥。可以理解,因为是国家文物,大家毕竟有顾虑,所以现在我国的唐琴大都锁在柜子里,而且大概率还要继续锁下去。我推动这个课题为老琴的重新发声做了努力,以后还会继续努力下去。可知,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并不容易。
以上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三大传统,我们的今天从传统中来,明天也必将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开创出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田青,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本文系作者2023年9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人格与治学”系列讲座上的发言,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