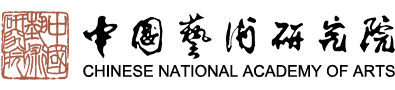胡仰曦
1981年6月出生于上海,籍贯安徽绩溪。2003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外文化综合班。2006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毕业。2006年至今,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杂志社。出版专著有:《一颗清亮的大星——胡适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痕迹:又见瞿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译著:(日)羽田圭介著《十九岁的夏天》,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在《新文学史料》《百年潮》《传记文学》《青岛文学》《钟山》《作家》《读者》等刊物发表人物传记、论文、小说、散文等。
痕迹:又见瞿秋白
瞿秋白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政治的先驱,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他在现代中国文学领域的不朽建树,特别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建设深深地影响了一个时代。而他本人潮起潮落、多姿多彩的一生也为中国新文学的画廊平添了一层瑰玮幻丽和气味深长。瞿秋白的一生有一根“文学”的线牵引着,贯穿着,他的心灵史完全可以用文学的烛火来尽情观照,也完全可以用文学的笔墨来完整表述。——事实上瞿秋白本人曽考虑过用文学的笔墨为自己的一生作自传。被关押在福建长汀囚室中时,他曾草拟过一份《痕迹》目录(从“1. 环溪”到“31. 得其放心矣”一共31个题目)。
本书《痕迹:又见瞿秋白》的构思与撰写即是依照瞿秋白的遗愿设计与叙述程序,完全依照《痕迹》“未成稿”的纲目章节梳理人事,安排框架。试图摩挲拂拭,寻觅心痕、辨识真迹,透射出其内质的光芒的同时,梳理出诗人革命家一生的心路历程与历史坐标。利用瞿秋白每一寸文学的波澜,每一段美感的漩涡,借助瞿秋白每一句“诗”来塑造好瞿秋白的历史,更感性地、更感觉地,也更艺术地、更诗意地描画出他的心灵,镂刻出瞿秋白逼真的人生“痕迹”,不仅描摹全他的躯壳,而且透凸出他的灵魂。长袖善舞,情采风靡,为人境留下一轮高挂绝丽的长虹。
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家乡/001
1. 环溪/001
2. 大红名/005
3. 父亲的画/011
4. 娘娘/017
5. 宁姐/022
第二章 北平/028
6. 黄先生/028
7. 出卖真理/037
第三章 第一次赴俄/046
8. 饿乡/046
9. 郭质生/101
第四章 上海/112
10.丁玲和他/112
11.“生命的伴侣”/125
12.独伊/135
13.误会/141
第五章 武汉/159
14.蓝布袍/159
15.庐山/165
第六章 一九二七年年底/175
16.忆太雷/175
第七章 第二次赴俄/181
17.□□□ (暂缺)/181
18.“老爷”/188
19.忆景白/195
20.面包问题/204
21.夜工/213
第八章 退养时期/219
22.油干火尽时/219
23.做戏/226
第九章 苏区/257
24.那松林的“河岸”/257
25.真君潭(雪峰)/260
26.只管唱,不管认/265
27.淡淡的象/271
第十章 上杭/277
28.逃/277
29.饿的研究/282
30.不懂的/293
第十一章 汀州/304
31.得其放心矣/304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1935 年6 月18 日清晨,秋白像往常一样起身披阅唐诗,当三十六师特务连长余冰走进囚室,向他出示枪决命令时,他刚作成集句诗《偶成》,遂疾笔奋书,留下最后的绝笔。此时,三十六师部官兵百余人,正列队聚集在堂屋,等候军事法庭对人犯的最后宣判仪式。
担任审判长的吴淞涛当庭向秋白宣读判决死刑的布告,并询问秋白:“如对家庭有遗嘱,可以当庭书写。”秋白泰然作答:“没有。”于是,吴淞涛命高春林宣读“审判笔录”后,即宣布:“将被告瞿秋白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高春林《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烈士就义前后》)
宋希濂与官兵们站在一起,全程目睹了这一场景,在《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经过》一文中,他有如下记载:“九时二十分左右,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他住了一个多月的小房间,仰面向我们这些人看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地走出大门。时间只是一刹那,但秋白先生这种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使我们这些人既震惊,又感动,默默离开了那间堂屋。”
当日,国民党三十六师令长汀园艺照相馆摄影师赖韶九和许萌秋在汀州中山公园待命拍摄。由囚室走到中山公园大约六七百步的距离。许萌秋回忆说:“一大清早,我们来到没有人影的公园里等候着。突然,从三十六师师部一个通向公园的边门走出一个中年人(后来才知道是瞿秋白),他身着黑衣白裤,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信步来到凉亭。当时,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已向他出示枪决令,但瞿秋白毫无惧色,轻蔑的笑了笑,说:‘人之工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随后,他悠然自在地站在凉亭拍了就义前之照。”(陈俊义:《珍贵的照片,历史的见证》,1980 年12 月15 日《北京日报》)
拍照之后,武装士兵在凉亭石桌上摆了酒菜。《大公报》记者在旁记录道:“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行至亭前,已见韭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憇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彼犹回首顾视,似有所感也。”(《瞿秋白毕命纪》,1935 年7 月5 日天津《大公报》第4 版)
从中山公园到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一片草坪上的刑场有两华里多山路,宋希濂出动了一百五十多人的特务连押送。卫兵们夹道戒严,荷枪实弹,气氛极为紧张。队伍前列有号兵一班吹号前进,最后有一个凶相毕露的“监斩官”陈定骑着高头白马尾随押队。秋白上身着杨之华亲手缝制的中式黑色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足登黑线袜。手持香烟,神态自若,从容缓步而行,沿途还唱起《国际歌》与《红军歌》。
据宋希濂转述蒋先启的报告,到达罗汉岭刑场后,秋白向在场的人作了十多分钟的演讲,大意是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是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使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他相信这个理想迟早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实现。临行前,秋白对执行者提出了两点要求:一不能屈膝跪死,而要坐着;二就是不能打头部。
最后的时刻,秋白环视罗汉岭四周,只见山上青松挺秀,山前绿草如茵,便点头微笑道:“此地很好! 就在这里。”他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昂首阔步走向最终的地点。用尽力气,仰天高呼:“共产主义万岁!”最后,盘膝而坐,静待子弹穿过心脏,当时的时间为1935 年6 月18 日上午10 时左右……
9 月1 日,左联后期机关刊物《文艺群众》在其创刊号上刊登了中国国内第一篇悼念秋白的文章《悼瞿秋白同志》,署名“本社同人”,全文约有三千字,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文中写道:
中国无产阶级的天才领袖,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光芒万丈的巨星,中国青年十多年来的最亲切的指导者,我们的瞿秋白同志于今年六月十八日在闽赣的边界,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战线,被国民党蓝衣团领袖蒋贼谋杀了!
几次报纸的传载,说他被捕了,我们不相信,我们说没有的事,他是不会被捕的。然而报纸的传闻一天天更加多,而且更加详细了,显然和平常的造谣有些两样,而我们也微闻闽西方面的确有部分的失败,我们说,不会吧,他是不会被捕的。说这话,已经有些不能自信,在统治阶级垂死的挣扎的瞬间,在这种空前的白色恐怖之下,一切都有可能的。然而我们实在不愿意相信他的被捕的确实,一直到我们看到了他的遗体的留影,穿着宽阔的中国衣衫,静静的躺在长汀草地的时候。
是的,他们枪杀了他,枪杀了我们最伟大的英雄,最亲切的领袖!我们永远记得,中国无产阶级劳苦群众永远记得的!
苏联也很快发布了秋白英勇就义的消息,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成员皮克、贝拉·库恩、马·卡申、曼努伊尔斯基、克诺林、科拉罗夫、库西宁、加·波利特等分别为共产国际悼念秋白的专号墙报写了悼念文章,都对这位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国际反帝联盟领导人之一表达了深切的敬意。他们指出了秋白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杰出功绩,谈到他的英勇精神,并一致认为他的牺牲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亦指出,秋白之牺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巨大损失”,称赞秋白“是中国人民为社会、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光辉榜样”。
在秋白殉难周年祭、两周年祭以及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以专版、专刊、纪念文章、党建课程等各种形式纪念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秋白。
最后,让我们引用毛泽东在1950 年12 月31 日为《瞿秋白文集》题写的一段题辞来结束全篇,虽然这段珍贵的话语在文集正式出版时(当时只出版了“文学编”)被神秘地抽掉了,重见天日已经是中国文坛拨乱反正文化复兴的新时期,然而其措词含义深刻,寄意悠远,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其核心意思仍然值得我们细细咀嚼、领会与诠释: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