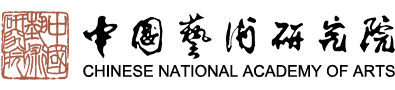李一赓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并在英国萨里大学完成了戏剧研究专业研究生的进修。自2013年起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以来,发表了十数篇艺术评论,业余时间一直从事话剧及影视编剧工作。
情感中的巨人 法理中的困兽
2018年根底下,被国家话剧院原创话剧《特赦》撞了个满怀。原本没赶上首演,却已从各个渠道获悉了此剧如何之优秀的信息。待亲眼观之,旋即加入了为《特赦》摇旗呐喊的队伍。作为2018年的收官之作,毫无疑问,国家话剧院为中国话剧舞台贡献的一部高质量作品,若精加雕琢,凭借此戏的剧本、调度、舞台等各个方面的优异表现,足以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本文发表于《中国戏剧》2019年第2期。
《特赦》一剧围绕着民国一段传奇故事展开——施剑翘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而后国民政府在民众与舆情的夹击下,特赦了施剑翘。原本历史上的故事就已经给故事提供了无限可能,而编剧徐瑛却没有美化那些边边角角的人物志异,而是通过司法的审判直击整个事件的内核,“为父报仇”到底是可以法外开恩?还是要严格执行司法审判?原以为故事的走向会像《哗变》一样,出现一个像格林渥一样的律师力挽狂澜,全剧是围绕着法庭展开,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几场庭外的戏,将两个失去父亲的角色塑造的惟妙惟肖。
施剑翘,一心为父报仇,抛夫弃子,面对亲人的推诿,丈夫的苦劝,依然选择了以暴制暴一条不归路。这位民国奇女子在获得了舆论与民心的绝对支持下,也丝毫没有“膨胀”。她的执念令她疯狂,但她也只有这一条执念。
孙家震,孙传芳的长子,为了将杀父仇人施剑翘置于死地,也斡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可最终他却没能得到法律和舆情的青睐,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施剑翘被特赦,无奈饮恨。
该剧最精华的地方,便是将“杀父之仇”所带来的影响,在这两个人身上分别体现。或许猛一看,施剑翘与孙家震处于一种绝对对立的层面上,但细心品味下发现,施剑翘和孙家震更像是二位一体。孙家震便是当年的施剑翘,而施剑翘便是沉淀过后的孙家震。编剧徐瑛用这两个立场截然相反的人,在情感上达到高度统一:孙家震为报父仇不惜代价,病急乱投医,最终却无奈收场;施剑翘经过多年的隐忍,已经被复仇二字占据了身心,面对死亡也淡然处之。故事用同一时间线上的两个人物,将人类内心深处、无法被法律庇护的仇恨,纽结在一起。
在这场情与法的斗争之中,永远也找不到双赢的办法,历史上也是一桩已经盖棺定论的案件,但这个故事偏偏巧妙在结尾处——孙家震持枪冲到施剑翘面前,却没有选择杀死她。纵然孙家震已经无法面对自己的亡父,他也并不是害怕牢狱之灾,但他还是“特赦”了施剑翘,不仅是这一具凡体肉身,而是从精神上“特赦”了人性的弱点。亡亲之痛在任何人身上都是相同的,编剧却在故事的结尾将两个情感上统一的人再次剥离开,同样的苦难,不同的选择。正是这种不同,让观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无论是法理还是情理,纵然有万般无奈,最终让人成为人的,还是每个个体的自我选择。遁入空门的复仇者算不算是一种精神惩戒与自我救赎?
《特赦》的剧情毫无疑问是近年来话剧舞台上难得一见的原创佳作。线索清晰,结构合理,在不去戏说的前提下,深刻挖掘出几个主要人物的核心,并将至清晰的表现在了舞台之上。同时剧中几句台词也颇具画龙点睛的功效,更让这些人物惹人喜爱。
新时代导演的蜕变之作
作为《特赦》一剧的导演,李伯男向观众们展现了他超凡的导演功力。回顾李伯男的导演作品,《有多少爱可以胡来》、《隐婚男女》、《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等等,无论在风格基调与商业运作上,都是可圈可点的,但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这些作品风格近似,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搞笑段子的罗列,堆搭出一个让观者哈哈一笑便抛诸脑后的小品剧。就在这种轻喜剧、生活剧的风格像一个牢固的标签贴在李伯男身上的时候,他却导风一转,拿出了这样一部作品,不仅推翻了一切加之于其身上的刻板印象,还将他积累多年的深刻底蕴爆发了出来。
一直以来,中国主流话剧界的作品,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所牢牢控制。无论是戏剧教育领域,还是各大省市院团,甚至国家话剧院,无一例外的沿用斯坦尼式的风格:大幕拉开,精致的布景,写实的基调,演员们“浸入式”的表演,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严肃题材。纵观新中国话剧史里的佳作,《雷雨》、《茶馆》、《狗儿爷涅盘》等等,基本都是大幕拉开后,观众们便“被迫”进入到彼时彼刻之中。虽然也有一些实验作品偶尔出现,或是艺术手法太过超前,或是叙事能力过于薄弱,问题层出不穷,禁不住时间的考验,最终无法留在舞台之上。
《特赦》一剧从大幕拉开的第一刻起,就没有让风格落入斯坦尼的模板之中。李伯男导演成熟的演员调度和对空间的把握,激发了观者大脑的飞速运转——笔者作为观众中的一员,脑中在疯狂的思考着舞台上出现的各个元素是何用意。背景屏幕的运用既没有沦为写实主义的布景板,也不存在过于写意的意向,每一次大幕的变幻都恰到好处的为角色的情绪服务,为剧情的进程服务。
全剧中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在这严肃的正剧之中,加入了风格化的表演,也就是孙家震这个角色。孙家震的角色由国话的青年导演石震扮演,这个角色从理论层面上来讲是十分难以拿捏的。一个军阀的儿子面临父亲被杀,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按照斯坦尼式的训练方法,作为演员如何才能表演好这个角色?稍有不慎,这个角色都会成为全剧的败笔,毕竟对于这种角色的认知,每个观众都有不同的见解,单纯的“写实”只会引起更多的分歧。李伯男导演没有将孙家震这个角色推入“体验式”的巨坑之中,而是用他最擅长的风格化、类型化的导演手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玩世不恭的公子哥是如何面对杀父之仇。从故事开始孙家震的信誓旦旦又有些轻佻浮夸,到剧中气急败坏却又心怀不甘,直至最后复仇无望濒临崩溃,将角色的情感变化演绎得十分到位。笔者并不反对“体验式”的表演风格,也非常了解斯坦尼体系下的演员塑造角色的功力,但对于《特赦》这出戏,孙家震这个角色的处理是非常成功且到位的。原本作为一个蔑视法庭、无视他人的公子哥,很难得到观众的青睐;但正是这种略微夸张的表演方法与他内心的纠葛产生了碰撞,成倍放大了角色的情感波动,最终让这个角色选择结束冤冤相报的时候,更具有震感力。
另外,《特赦》一剧中出现了大篇幅的中国戏曲元素。在中国戏剧艺术领域,数十年来一直在探索中国戏曲与话剧相结合的议题。既有把中国戏曲元素当作故事背景的话剧,也有“话剧加唱”形式的中国戏曲,这样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但终归乏善可陈,好作品屈指可数。而在《特赦》一剧中,戏曲表演成为了情节中的一部分,完美的贴合剧情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理解故事有推波助澜的功效。这样的话剧与中国戏曲相结合的方式,既符合历史情境,又让观众在风格中间离,在情绪中浸入,交相辉映,绝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跨界合作”。
李伯男导演让观众看到了严肃历史题材话剧在表达上的新的可能,他用积累多年的舞台剧导演经验,给观众展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观剧体验。《特赦》可以说是李伯男的集大成之作,这种蜕变标志着他在舞台剧导演艺术上的成熟,让人不禁期待其下一部作品是否可以更上一层楼。
舞台空间的新探索
《特赦》一剧在舞台空间上的运用,也是一次“出乎意料之外”,又“合乎情理之中”的大胆尝试。
一分为二的舞台空间并不罕见,许多话剧都运用了这样的效果,但大多数时候,只是单纯的增加了调度的可能性,亦或是为写实而写实的存在。然而在《特赦》一剧中,舞台布景与故事剧情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全剧情节主要发生在寺庙、法庭两个空间,这两个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一些人们眼中共通的文化认知:严肃、规则、教条等等。而这些支撑着二层平台的立柱,等长等宽,间隔一致,迅速的将观众们带入到了空间之中,与那些存在于真实寺庙、法庭里的立柱形成了对应。在故事的进行中,被推上被告席的施剑翘单独坐在二层的高台上,纵然法庭之下争辩激烈,却始终没有让作为故事主角的她失焦。另外,大多数情感上的纠葛发生于舞台的二层,而将历史写实的部分放在立柱林立层叠的一层,也让观众在情绪上的切换得以充分施展,可以说这一次的空间分离成功与叙事相结合,指数倍增加了全剧的观感。
同时,该剧在对背景荧幕的运用上也别出心裁——它可以是庙堂之上的飞檐;也可以是灵堂中的遗像;亦或是故事内空间转移的提示;也能作为法官手中的判决。其实如何运用背景荧幕本是见仁见智,但该剧中却能将原本可以炫目斑斓的电子手段由繁入简,剥离掉那些可能会影响观众体验的电子讯号,将最核心的部分呈现出来。
这种介于写实和写意之间的舞台布景,让整个空间看起来非常高级。一直以来,舞美作为戏剧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任何创作者都不会忽视其巨大作用,但随着舞台艺术的发展,各种新式理论的层出不穷,再加上原本戏曲舞台就“重戏服轻戏台”等原因,舞美被边缘化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依笔者遇见,舞美其实是最需要和创作者们协同工作的部分。舞台设计刘科栋的作品一直以来都为人津津乐道,在业内更是享誉盛名,而这次《特赦》一剧完美的将剧情与舞美无缝粘连,既有奇思妙想的细节,又能展现出大巧不工的气魄,可以说是舞台布景中的标杆也不为过。
写在故事之外的
笔者离开剧场时,偶听到一位观众说起此戏“三观不正”。思考良久,还有些感悟不吐不快。对于作品与观众之间,其实本没有什么“三观不正”。三观只有合与不合,并无正反可说。剧中角色对于仇恨的理解与反应,本就是基于个人的选择,而戏剧舞台就是将其中一种或几个可能性,呈现在观众面前,供人评说。很久没有看到这样能引起观众们热烈讨论的原创话剧,中国国家话剧院这一次展现出了作为“国家队”的担当,能以足够的艺术品格,搭建起精致的平台,吸引广大戏剧爱好者,甚至是普通话剧观众,对故事产生思考,对人性进行探讨。这是戏剧最原本、最核心的魅力。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国家话剧院能带来更多更好的戏剧作品,从《特赦》中,笔者看到了中国原创话剧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值得所有话剧艺术工作者们学习的榜样:从1907年起,至今111年,无数中国话剧人前仆后继的将这“舶来品”本土化,纵有千难万难,也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再创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