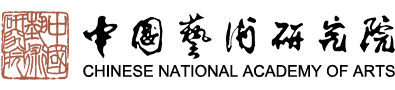郑长铃
郑长铃,男,1962年生于福建宁德,中共党员,博士,研究员,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发展战略、文化艺术新型智库等研究。担任文化部科技司委托课题《智库类型分析与文化智库模式研究》及本院多个课题的负责人。著有《大乐天心续编》等,发表论文、评论百余篇。曾担任“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副主编、《“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主编。
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的双视角研究
“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研究可有两个维度:一是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即不仅要关注中华文化的向外传播,也要梳理外来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二是“陆丝”与“海丝”的关联研究,即以中华文化中心由西北向东南移动的大势为背景,将“海丝”与中国历史文化大动脉——大运河结合考察。本文从上述两个维度出发作历史追溯和现状观察,认为此领域的全面深入研究,对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意义非凡,理应得到重视。
该论文为作者与陈宇峰、黄欣合著,发表于《“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一、题解
“双视角”研究理论是一种以人类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最初由美国的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1]于1947年提出,并于1954年在其出版的《论语言与人类行为的统一原理》[2]一书中系统阐释。该理论要求研究者在观察文化事象时,同时以“局内人”和“局外人”两个身份来考察。也就是说,既要以“局内人”的身份视角深入到文化事象内部,去直观地感受和体验;也要以“局外人”的身份视角跳出该文化事象,站在一定的高度去重新审视它。
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这种“双视角”研究方法又被称为“音乐文化的双视角观照”。该研究方法的核心就是兼具“局内人”与“局外人”两种视角方法去观察研究对象,以便得出科学、全面的结论。
站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得到的结论可能不尽相同。如面对“饺子”的时候,欧美研究者以“局外人”的视角审视它,中国研究者以“局内人”的视角考察它,得到的结论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对饺子的认知更倾向于“饺子是一种食物”的角度,而后者则偏重于其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符号背后的文化意义。同理,当面对汉堡、薯条这些从西方泊来的“洋快餐”时,中外研究者的认知也会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只有兼顾“局内人”和“局外人”两个视角,才能客观、公正、平等地看待“异族”文化和“我族”文化,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事象的意义,从而得出较为客观、全面的结论。
如今,“双视角”研究理念已成为语言学、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理论。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提及的“双视角”,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学或民族音乐学中的“双视角”概念,只是笔者借用了“双视角”研究之理念与方法——即在观察文化事象时,虽不能同时兼具“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但可以通过多维度的内、外视角,从不同层面去观察研究文化艺术事象。
二、“一带一路”的回顾与展望
(一)“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
“一带一路”全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发表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伟愿景;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讲话,进一步提出推进丝路精神由陆至海的伟大倡议。
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3]。《愿景》指出: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这些贯穿亚洲、欧洲和非洲大陆,连接着几大经济圈的经济带,正是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而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都有着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留存,因此,在分析“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时,笔者引入了“文化线路”这一概念。
1993年圣地亚哥线路被列为世界遗产,这应该是“文化线路”这一概念最早被提出。2008年10月4日,第16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正式通过了《文化线路国际宪章》,该宪章的通过标志着“文化路线”正式成为一项新的文化遗产类型。“作为遗产类别,‘文化线路’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动态特点的结果,它们是人类造就的或使用的、有特定的具体目标的历史环境。所以,‘文化线路’中的遗产,展示的是具体和特有目的的人的流动和交换的具体现象。它们不仅包括促进其流动的有形线路(到目前为止,仅为有形线路),而且还包括线路中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实体和文化价值。这些遗存与其具体目的和历史功能相伴共生。”[4]
“文化线路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随着不同人群在一定空间(线性或非线性)上产生的具有目的性的流动交往行为,继而在产生了跨文化碰撞与整合作用的同时,于有形和无形遗产基础上,以文化传播或文化涵化的显形或者隐形的路径为线索,形成的具有一定类型特征的文化意象和遗产保护、城乡规划的视角。”[5]
(二)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与回顾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费尔迪南·冯·李希霍芬[6]提出,李希霍芬于19世纪末在其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7]中首次使用seidenstrasse(“丝绸之路”)这个德文词汇。丝绸之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相对于“海上丝绸之路”而言的“陆上丝绸之路”,而广义的“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合称。在本文中所提到的“丝绸之路”均为狭义的陆上丝绸之路概念。
关于丝绸之路的开拓,学界目前认为其最早可溯源到远古年代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地处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东起乌鞘岭北面的古浪峡,经武威、张掖、酒泉,到最西面的敦煌玉门关,总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8],宛若一道狭长的走廊,故而得名。
西汉初年,匈奴对西北边疆地区的侵扰,不仅使西北边疆地区灾祸不断、生灵涂炭,也严重威胁到了汉都长安的安全。汉武帝时期,为了联合西域共御匈奴,遂派张骞出使西域。虽然张骞未能顺利完成使命,但是却探明了西域的情况,开阔了汉对西域的认识,也促成了汉武帝通西域的决定。为了更好地抵御匈奴侵扰,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立酒泉、张掖、敦煌和武威四郡。四郡的设立捍卫和巩固了西北边疆的安全,逐渐成为维护和保障使臣出使西域的重镇。
汉朝和西域通使,使河西地区成为连接汉与西域的重要通道。政治的稳定、经济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域将棉花、葡萄、胡桃等农作物传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域的良马,大大提升了中国骑兵的作战能力。而中国的印刷术、火药、造纸术、指南针、金属冶铸、穿井技术、瓷器、丝绸等也经由此路传至西方,尤其是丝绸等丝织品源源不断地销往中亚和欧洲,“丝绸之路”因此得名。
丝绸之路的兴起带动了经贸的繁荣,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记载: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9]
丝绸之路的繁荣在促进经贸交流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中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西域的音乐、舞蹈、宗教艺术等沿着这条路传到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音乐、儒家思想等也传到了西方。
“文化的交流实际上是各民族在各种形式的交流中相互影响,并分别作出各自贡献的过程。”[10]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域的文化上:这些文化,既受到了来自中原文明的因素影响,同时又有着来自印度、中亚、西亚文明的影子。
中华民族在与外国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从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新文化。西北地区的石窟艺术就是典型的例子:“像面安详,双目微闭,鼻梁直通额际,发呈波状等。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衣褶用醒目的凸线表示,从身体突出部位下垂,优美自然,既表现出衣物的质感,又显露出身体轮廓。这种犍陀罗风格,是古代东西方两大艺术体系相互影响的证明。”[11]
这种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谁替代了谁,也不是完全意义的一律兼收并蓄;而是从外来文化中多角度、多方面地吸收自己需要的部分,汲取有利于自身文化发展的营养,从而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促进文化繁荣。
(三)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与回顾
“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是由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于1968年在其著作《中国瓷器之旅: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12]一书中提出,取代了之前的“陶瓷之路”。
作为中国古代与外国交通、交流的另一条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一般被认为形成于秦汉时期。西汉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促进了西北边疆地区的发展,但是到了新莽时期,由于西域诸王与新朝中断关系,致使中西方陆路交通受到阻碍,促使海路进一步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可以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部分:
东海航线是指经由黄海、东海的海路,最终抵达日本、韩国、朝鲜等国的线路。最早可以追溯至周武王派遣箕子东渡朝鲜,传授养蚕织作。到了秦始皇时期,派徐福率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并传播养蚕织作。这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早期形成。
而南海航线是指以徐闻[13]、合浦[14]、广州、泉州为起点,经南海到达东南亚各国,并逐渐延伸至印度洋、波斯湾甚至非洲大陆的这条线路。在后文中,笔者提及并着重阐述的“海上丝绸之路”即为此条航线。
《汉书·地理志》记载:
“自日南障塞[15]、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16]
《后汉书》卷三十三《郑弘传》记载:
“建初八年[17],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18]贡献转运,皆从东冶[19]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20]
隋唐时期,西域的战乱再一次阻断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借此再次兴起。到了两宋,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加之造船和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彻底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了我国与外国交流的重要通道。此时的福建泉州因为充分发挥其挟南北两路对外交通之利的地理优越性,成为东南沿海诸港口无法匹敌的“东方第一大港”。
据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
“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21]
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除了向海外运送丝绸之外,还向海外输出大量的瓷器,如泉州德化的瓷器、福建北部建窑的瓷器、浙江的处州窑[22]瓷器、江西的景德镇瓷器等。因此,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作“海上瓷器之路”。
明代初期,为了巩固统治,明政府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海禁”下的朝贡贸易成为了当时的对外贸易政策,虽然严禁私人出海,但是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贸易,无疑使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巅峰。从明永乐三年[23]至明宣德八年[24]的28年里,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先后到达的国家多达30多个,在进行经贸交流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四)“一带一路”研究中的问题与思考
文化的传播总是相互的,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当大量海外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大量优秀文化也得以输出海外。但是,在现阶段的相关研究中,不难发现研究的重点偏向于文化的向内传播,即在通过“陆丝”和“海丝”传入到中国的文化;而中国文化通过“陆丝”和“海丝”的向外传播,却是当今研究之中的弱项。如《2016“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5]中共收录论文63篇,其中收录中国大陆学者论文55篇,台湾学者论文3篇,海外学者论文5篇。而在55篇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中,对传至海外的中华文化存续现状研究的论文仅有5篇。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艺术相关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要秉持内外兼顾的“双视角”理念,即在研究西方文化向内输入的交流和传播的同时,也要兼顾到中华文化向外输出的交流和传播。
与此同时,即使是在“双视角”的理念下研究“一带一路”文化艺术的相关问题,也不能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割裂来研究。就丝绸之路只研究“陆丝”的相关问题或者是就海上丝绸之路而只研究“海丝”的相关问题,难免会出现研究过于片面的弊端。因此,善于发现其中的联系,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成一个整体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尝试。“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认定为洛阳,同时也是中国大运河上一个重要城市,而大运河的终点业已认定为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就此,形成了一条由丝绸之路和大运河连接而成的中国古代与世界交流的大通道。”[26]这条大通道不但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为一体,同时也促进了国内文化的交流、传播与融合。这便是本文“双视角”研究中的内部视角研究,即研究“一带一路”文化艺术由外向内和由内向外的双向研究的同时,也要关注到两条“丝路”内部的联系。
三、“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最早起源于吴王夫差时期开凿的“邗沟”,后在邗沟的基础上逐步向南北两侧延长,成为了今天的大运河。
吴王夫差于周敬王二十四年[27]即位,直至周元王三年[28]去世,在位22年间,筑邗城、开邗沟、破越败齐、开发长江下游一带,逐渐成为春秋末期的一位霸主。为了北上伐齐,他下命在扬州到淮安开凿一条沟通长江和淮河的运河——邗沟。
清乾隆《淮安府志》中记载:
“春秋时,吴将伐齐,与邗江筑成穿沟,曰渠水。首受江于江都县,县城临江;北至射阳入湖。杜预云:自射阳西北至末口入淮,通运道。其水乃自南而北,非自北入南也。”[29]
到了隋朝,统治者为方便调兵及沟通南北漕运,在前代运河的基础上加深和拓宽,同时开凿一些新的运河,并将它们与之前的运河连接起来,一条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由此形成。这条大运河西达长安,北至涿郡[30],南到余杭[31],总长2000多公里,将黄河、海河、长江、淮河和钱塘江五大流域连为一体,形成了以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为轴心,向东北、东南辐射的水运网络。不但实现了统治者最初调兵和漕运的目的,也加强了南北的联系。
在大运河尚未贯通南北之前,我国的文化发展呈现出来的一直都是北强南弱的不平衡局面。从商周时期开始,中国的文化中心就一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到了西汉,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繁荣,西北地区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地发展。隋唐时期,大运河的贯通加速了文化中心由北向南迁移的进程。直至两宋,文化中心由北方的黄河流域南移至江淮流域,并最终移向长江以南。可见,大运河的开通对南北方文化的交流和平衡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艺术作为文化最直观的表象,是南北方文化传播、交融与互动的生动体现。
“大运河这条交通和经济的大动脉,把古代中国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与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把西北关陇军事重镇与江南财富紧密联系在一起;”[32]同时,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也连为了一个整体。更值得一提的是,大运河也为中原人南迁东移提供了可能。无论是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中后期的“安史之乱”,还是北宋时期的“靖康之乱”,历史上每一次大动乱都会导致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而在每一次大规模迁移中,水运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在这一次次人口迁移的过程中,文化艺术也得以“艺随人走”。从隋唐到两宋,政治中心沿着运河逐步从西北移向东南,而中原的乐舞也通过同样的路线,传播至东南地区。同时,正如前文所述,文化艺术的交流与传播总是相互的,中原文化传至江南的同时,南方的文化也得以传到了西北。随着运河的走势,文化艺术的传播和交流也呈现出了自北向南、自南向北的双向传播的局面。
在促进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同时,大运河的开通也促进了沿线城市的崛起,市井的繁荣促使那些从中原传来的宫廷文化艺术逐渐走向民间。而这些走入民间得以发展和“再创造”的文化艺术,又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重新回到宫廷,这就造成了文化艺术交流、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循环。与此同时,那些沿丝绸之路从西域传来的文化艺术,经过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早已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表现形式,这种新的文化表现形式,也通过大运河传播至东南地区,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这些文化艺术也可能重新传播回海外,造成文化艺术交流、传播过程中的另一个循环。这两个循环能够成为可能,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功不可没。
上述两种循环的发现,正是由于在研究“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传播问题的过程中秉持了“双视角”的研究理念,即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去观察文化事象、思考相关问题。
四、总结
无论是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还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在加深经贸往来的基础上,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推动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沟通和心灵上的碰撞。而在这个过程中沉淀至今的沿线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在这条大的文化线路中与历代民众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实践。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求同存异、和谐共存的“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以及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天下大同”的历史责任感。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33]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使命,从时代潮流、历史地理禀赋、现实需求、沿线国家人心聚合等因素来看可谓恰逢其时、充满机遇。”[34]而新时代的文化“丝绸之路”,不但可以促进经济贸易的交流和发展,更能凸显文化的交流,从而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今天,在推动“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时,我们不仅要以史为鉴、继承传统,更要结合今天的时代特点,加大力度讲好中国故事,做好相关的研究,从而更好地促进民心相通,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涵化外来文化,取其精华、洋为中用,以便更好地促进我们的发展、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
[1]kenneth l. pike(1912-2000)
[2] [美国]kenneth l. pike,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m],berlin: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1967。
[3]以下简称“《愿景》”。
[4]丁援.《文化线路:有形与无形之间》[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5]丁援.《文化线路:有形与无形之间》[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