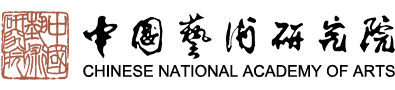孟 潇
孟潇,文学博士,助理研究员,涉及艺术文化学及中国古代思想史。主要作品《废墟上的引灵:当代艺术家的语言变形记》《遇与言:以〈传习录〉为论说中心》《〈女巫吉孜特尔娜克〉的细读笔记》《与万物共在:沈苇诗论》《砾石中的微神:蓝蓝诗论》《〈开•闭•开〉:阿米亥全书》《思想的故事性》《虚实之间的田园:训释、缘起、意涵及其他》《格则多吉:泸沽湖隐微变迁的记忆者》《阅读的秘密行为》《<巴扎志>行旅》《波兰之光》等。
戏剧是“一” 世界是“三” ——有关“新剧场”岁末读剧之《一赶三》
剧作《一赶三》的题名,本是中国传统戏曲的术语,这个以在中国戏曲中标明演员表演形式和能力的传统术语剧名,讲明了戏剧手段或者技术,是表演功力的展示或者训练。像是一次编剧的戏剧试炼,既是编剧对一种戏剧手段的试水,也是对想象的演员可能的锻炼。编剧在题记中给予了这个名目一个功能性的解释,即“试图运用这种形式,让一个女演员和两个男演员,在一个大的时空背景之下,分别饰演三个社会层面里三个女人和六个男人的生活场景。它可以让观众看到特定处境中一些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矛盾纠葛、喜怒哀乐,也可以让演员多方面展示他们的表演功力。”但笔者在分析剧作时,以为“一赶三”这一题名其实对戏剧有着更深的揭示,并有着更高的哲学意涵。即戏剧若是“一”,世界就是“三”。你在“一”中会看见“所有”。戏剧从一个人的处境,一个人的悲剧,最终会进入所有人的悲剧。一个人悲剧性的死亡,也许意味着全人类的死。
本文发表于2018年2月《山东艺术》。
去岁的最后七天,在北京的蓬蒿剧场,连续观看了七场“新剧场”的读剧活动。除了开幕剧《三口之家》是去年的优秀剧目,其余六个剧本是从各地创作者所投递的近六十个剧本中优选出的。索健的《三口之家》与阎美宁的《心魔》是有关家庭伦理与生活困境的,赵大河的《朱丽的欺骗》与李向的《一节只有两个学生的课》是有关世相与人性的,张印的《薤露歌》是有关对历史现场的想象与解释的,王明端的《经过瓦拉尔》是一个没有时间感,诗一般的,以松鼠、棕熊和钓鱼人为主人公,探讨人们在虚拟空间遭遇的剧作,而茅歌先生的剧作《一赶三》是读剧会的最后一场。这是一个初看题名,不明所以的剧作。何者为“一”?何者为“三”?又如何去“赶”?一出剧作,何以用戏曲术语为名?难道“一赶三”这一戏剧手段在这个剧本里是更被看重的问题吗?
其实之前对“一赶三”这个在中国戏曲中标明演员表演形式和能力的传统术语作为剧名感到疑惑,一个讲明了戏剧手段或者说技术的题名,会给一出剧带来什么呢?这是一个表演功力的展示或者训练吗?它高于文本的意义吗?这个题名,像是编剧的戏剧试炼。既是编剧对一种戏剧手段的试水,也是对想象的演员可能的锻炼,编剧在题记中解释这个名目,“试图运用这种形式,让一个女演员和两个男演员,在一个大的时空背景之下,分别饰演三个社会层面里三个女人和六个男人的生活场景。也许,它既可以让观众看到特定处境中一些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矛盾纠葛、喜怒哀乐,也可以让演员多方面展示他们的表演功力。”但这样一个功能性的解释始终没有满足我,因为每每想到“一赶三”这个题名,我总觉出特殊的意味。
看读演剧作《一赶三》是在一个下午,吃过午饭有些饮食困,一入剧场看到台心的可移动换衣架上一排各式各样的衣服,才醒觉了些。之前没做功课,不知道本剧的读剧导演是何雨繁,一人扮演三个女人的演员是之前看过她很多演剧的阮思航。虽是读剧,此剧的人物都是齐整的,服饰妆容,表演情绪,剧场声响、音效、灯光的布置都是细致的,读剧导演和演员的用心,随着第一幕城市贫民区的一个陈旧院落里杨翠花故事的生猛展开,完全叫醒了我。
三幕剧分别写了三个女性,她们是战争年代丈夫出门两年未归、杳无消息、不得不寻求依靠的中年村妇,是饱受生活摧残的、却曾对生活充满热望的妓女,是处于死水般生活庸常、快要窒息的知识女性。她们并不像契诃夫写作的《三姊妹》那样陷于生活的泥沼而对另外的世界始终抱持精神性的向往,她们只是在自己有限的生活局面中,回护着自身的伤痛,有着最低的盼望,她们各自并没有生活的交集,却都是大时代、乱世界飘零无根的人,她们有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面目,却也有着自身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上所做的决定。她们也不像奥地利作家穆齐尔在由三个短篇小说构成的《三个女人》里写的格里吉娅、葡萄牙女人、佟卡那样,是迷惘、孤独的男人所渴望的非理性的力量,此剧中的她们就是在她们那独一的幕中活着,她们周身的男人都只是陪衬人,甚至她们的性别都不是重要的,她们只是被剧作家方便地写成了女性。她们是一个时代被忽略事物的共同缩影。她们微小的痛苦被忽略,她们的处境细小在生活的角落,她们只是承受、忍耐着度日,她们不知道明天是怎样的。但令人欣喜的是,她们在此剧中难得地拥有了选择。她们的选择,在她们微小的处境中甚至是清晰而坚定的。她们的形象并不十分可爱,但在某些时刻,她们会让人生出些许敬意。
剧作者将这三幕剧的时间设定在“1940年代”,地点写做“中国乌有市”,“乌有市”意味着这三幕剧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而“1940年代”意味着民国末年,战争,动荡频仍的时代局面。三幕剧中的三位女性主人公,分别是住在城市贫民区的中年妇人杨翠花,生病住在医院里的妓女李玫,出入于办公室、家和监狱的律师马丽。杨翠花,因丈夫出门经商音讯渺无,在冬日年末的破败院落更显得孤独无依,她独自一人拉扯一个刚刚上学堂念书的女儿,她的邻居牛哥是常常来帮她干活儿的人,牛哥挑柴禾,一个底层妇女给予牛哥唯一可给予的回报,但房东文先生却是杨翠花对未来可能生活唯一可指望的稻草,她羡慕文先生有两个未来可倚靠的儿子,她对生活的希冀来自新的可能的孕育对长久缺位丈夫的代续,没人知道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她久未归家的丈夫是否可以活着回来。此目作为世相之一片,煞尾于一个低沉、虚弱的男人在一阵激烈的咳嗽声之后的询问——“请问,杨翠花还住在这里吗?”非常令人意外的收煞,却给人了一点希望。一幕灯暗,演员们在台上换装,坐定。第二幕灯亮,演员还是之前的演员,人物装束、神情为之一变。李玫,一个风尘女子,被帮派大哥爱慕的女人,内心深处有着不为人知的剧恸,她早夭的,死于饥困与病痛的孩子,以及自己的身世之悲,让她对生活全无希望,而她身旁的照拂她的大哥和小弟都是背负冤仇的苦命人,每个人身上都有深深地担负,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此目同第一幕的收束一样,是意外而迅疾的。人群的喧声,警笛声,枪声,随声响与喊叫冲出去的帮派大哥不知是否还可以全身而回?二幕灯暗,演员在台中心换装,坐定。第三幕灯亮,秋日雨夜,监狱囚犯出逃,野外抓捕,引出警察局长的家庭场景,律师马丽和她的局长先生,像是两个陌路人,他们说起家事,像是讨论公事,而在家谈公事,却需要动用私情,一个失心的家庭,却因需要特殊严办的案件维系,然而颠倒黑白的不只是案件,还有马丽与丈夫颠倒公私情境的让马丽感到窒息的人生,而与案犯刘一氓的交谈,却开启了她另外的精神空间,他们两个人互相帮助并互相启迪着,逃出了各自的或肉体或精神的监狱。
三幕剧像是对纷乱世相之断片的截取,生断而各自独立。每幕中活色跃动的男女情事,配合着或是院落中的鸡飞狗跳,或是歌舞场中老唱机的旧情调,甚或京剧唱段《苏三起解》所诉的身世之悲,显现着人间生命不灭的征兆,而神奇的有了内在的关联性。我偶然想到几年前来中国的巴西剧场《三个悲剧女性》中,巴西剧场人为古希腊悲剧的里三个女性安提戈涅、厄勒克特拉、美狄亚树立了充满仪式感和光感的具有丰沛力量的独白纪念碑,却也更多地剔除了她们的人间性,让人间的悲剧女性成了天上的祭司。而茅歌先生的这个为普通零余者立书的剧作,写作了三位女性,或者说三个普通人,以及这三个普通人周边的人们,在他们非常具体的生活中无可回拒的困境,他们微小而巨大的悲喜,他们看起来无可逃遁的个人命运,还有那些可以想见的,他们的那些需要挨过去的,充满龃龉的大地上的一日,又一日。
至此,我忽然有些理解中国戏曲表现程式“一赶三”在这里作为题名的别样意味。“一”个演员,在一出戏中,演出不同的角色,转换不同的人生。这里,“三”,既是“三个女人”,也意味着更“多”的。戏剧若是“一”,世界就是“三”,就是“多”。你在“一”中看见所有,你会是所有的人——你会是杨翠花,会是李玫,会是马丽,甚至你也会是牛哥,文先生,菜刀帮帮主,菜刀帮成员铁蛋子,警察局长,蒙冤犯人刘一氓……诗人萧开愚写过《北站》,“我感到我是一群人”,诗人蓝蓝写过《我的姐妹们》,“一个女人,我的姐妹们,难道不是同一个?”所以一个人的处境,一个人的悲剧,就会是所有人的。一个人悲剧性的死亡,就是全人类的死。
此剧令人感佩的是,剧中的主人公都在一个时刻,做出了他们的决定。村妇杨翠花决心一试,她要为自己的余生做出努力,她是想生出一个像文先生那样会念书,待人亲切,又可以成为家中顶梁的儿子吧;病房中的妓女李玫决心不接受蔡大哥的爱意,她不愿再麻烦这世间的任何人;接手自己的局长丈夫提请特别处理的强奸案律师马丽决定与她认定的这个自由、浪漫的蒙冤无罪人一起离开她陈腐死寂的无意义人生,他们一起把马丽穿着不再舒服的鞋子扔向远处,他们的笑声回荡在空旷荒野。剧末,台上回荡的是两个获得自由的人的笑声,即使可能是短暂的自由,即使更大的,更不可知的未来正在到来。但剧作至此,仍然给所有的人留了一个通向空旷自由之地的气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