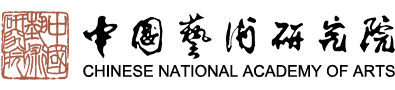王 慧
王慧,1974年生于山东。2005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古代、近代小说及戏曲的学习与研究。在《红楼梦学刊》、《蒲松龄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学术交流》、《中华读书报》等发表文章数十篇。著有学术专著《大观园研究》(200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学术论文集《红楼梦及其戏剧研究》(2018年12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等。
苏青与张爱玲的“天地”情缘
[摘 要]:苏青与张爱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滩著名的女作家。二人以苏青主编的杂志《天地》结缘,不仅发表了相当多的文章,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在上海滩留下传奇色彩的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情缘”也离不开苏青及《天地》。尤其是《天地》中被忽略的“生育问题特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两位女作家的人生轨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关键词] 苏青;张爱玲;天地;生育;胡兰成
最近在翻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滩的一些书报杂志,常常为其掌故逸闻感慨,尤其一份刊物及其特辑触动了我们脆弱的神经。这份刊物就是堪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滩两位当红女作家——张爱玲与苏青的写作重阵《天地》,其特辑就是《天地》第七、八期合刊中的“生育特辑”。苏、张二人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热点”;而“生育”问题更是当今社会的“症结”,要不要生?如何养?无所适从的我们究竟该怎样教会孩子保护自己免受这个并不都是善良之世界的恶意伤害?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当时声名鹊起的苏青与张爱玲的“天地”情缘,聊聊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孩子、尤其是对生育问题的看法,从尘封的故纸堆里追逐着曾经的脚印寻求一点点对今天的我们可能有用的启示。
一、“天地”情缘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滩横空出世了两位著名的女作家,号称“上海滩双璧”,她们就是苏青与张爱玲。
王安忆曾经这样形象地写到二人的区别:“她(指苏青,笔者注)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却是坐在窗前看。”[1]苏青是充满了俗世气息的,张爱玲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这样两个行事作风相异、作品风格内容也完全不谐、尤其是身处“那时那地”的女人,却也建立起了同性之间少见的友谊。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本杂志,即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天地》。
1943年10月,苏青开办了“天地出版社”,位于上海爱多亚路一百六十号六零一室,《天地》创刊号于同年10月10日出版,每册十元,10月15日再版。其首印3000册,出版后立即脱销,再加印2000册,又一扫而空。集社长、主编、发行人于一身的苏青风头之健可见一斑,不愧是当时“最红的两位女作家”[2]之一。而且以宁波人的精明,苏青还经常在《天地》的编辑发行中搞些噱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很有商业头脑,八折优惠、命题征文、作者玉照、各种特辑等等花样百出,一时间《天地》名声大噪,几乎成为沪上数一数二的刊物 。
苏青在1944年第19期《大众》发表的《做编辑的滋味》中曾介绍过自己创办《天地》是因为自己“热心投稿,但各刊物的编者却并不一定热心采用”,因此发奋将来也要做一个编辑。自1943年10月至1945年6月,苏青共编辑《天地》二十一期,近三百篇文章,她之所以给刊物取名“天地”,恰如她在《发刊词》中所说,“把达官显贵,贵妇名媛,文人学士,下而至于引车卖浆者流都打成一片”,不外是要将各路作者都聚拢来,谈天说地,无所不包。而《天地》的内容趣味也离不开常人“生活之甘苦,名利之得失,爱情之变迁,事业之成败”,大多是饮食男女的俗世生活,讲求人间百态,通俗易懂。
不仅如此,《天地》还因为苏青巨大的约稿能力,招揽了一批很受时人关注的作者,比如陈公博、周佛海、周杨淑慧、纪果庵、周作人、谭惟翰、柳雨生、秦瘦鸥、丁谛、实斋、陶晶孙、叶德均、施济美、周幼海、刘曼湖等。而苏青自己更是与张爱玲因《天地》结缘,留下了一段海上传奇。
在二十一期《天地》中,苏青和张爱玲几乎平分秋色,是最重要的作者。自第二期发表著名的小说《封锁》起,张爱玲在《天地》发表了大约十六篇文章,分别是《公寓生活记趣》(第三期)、《道路以目》(第四期)、《烬余录》(第五期)、《谈女人》(第六期)、《造人》(第七、八期合刊)、《打人》(第九期)、《私语》(第十期)、《中国人的宗教》(上、中、下)(第十一、十二、十三期)、《谈跳舞》(第十四期)、《“卷首玉照”及其他》(第十七期,第十五、十六期是1945年元旦出版的合刊)、《双声》(第十八期)、《我看苏青》(第十九期)、第二十期有张爱玲翻译的炎樱的《女装,女色》。《天地》的最后一期,虽然没有张爱玲的作品,却有署名“胡览乘”(即胡兰成)写的《张爱玲与左派》,依然有着张爱玲的身影。
尤其《天地》第十一期到十四期还采用了张爱玲设计的封面。《天地》之前采用的是谭惟翰设计的变形的“婆罗马”神,第十一期采用了张爱玲的设计。画面有天有地,还有几片云,一尊仰卧的、有着非常柔美侧脸的佛像,只画到脖颈下面,很有张爱玲笔下真正的女神“地母娘娘”温暖的气质,充满了“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在张爱玲看来,“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3],这个封面也更契合《天地》的女性柔媚气质。
苏青也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几乎每期都会亲自上阵,共发表了二十一篇文章,即《论言语不通》(第一期)、《涛》(第四、五期)、《买大饼油条有感》(第五期,署名“禾人”)、《谈女人》(第六期)、《救救孩子!》(第七、八期合刊)、《结婚十年后记》(第十期)、《救命钱》、《文化之末日》(第十一期)、《消夏录》(第十二期)、《谈男人》(第十四期)、《十一月十一日上午》、《“浣锦集”与“结婚十年”》(第十五、十六期合刊)、《如何生活下去》、《敬告妇女大众》、《心》(第十七期)、《谈婚姻及其他》(第十八期)、《敬凶》(第十九期)、《谈宁波人的吃》(第二十期)、《朦胧月》(第二十、二十一期)。
苏青的约稿能力令人吃惊。《天地》的许多作者几乎都提到了苏青百折不挠的邀约。周杨淑慧在创刊号的《我与佛海》中曾说苏青“再三劝说,每日催促,而且指定题目,不便拒绝”;予且在《我之恋爱观》中也对苏青甘拜下风,“她之讨稿,不但是限期限字,还要限范围出题目”。因此,在上海滩横空出世的张爱玲收到苏青以“叨在同性”为由的索稿信也就无可厚非了。以致张爱玲认为“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4]。
幸好,张爱玲紧接着说出了“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她与苏青之间的“天地”情缘深刻而又微妙。两人似乎是惺惺相惜的,苏青经常对张爱玲赞赏有加(如第二期《编者的话》以及第十四期《编者的后记》等),还给张爱玲的作品《传奇》、《流言》等做过广告,不吝赞美。在1944年3月16 日《杂志》举办的“女作家聚谈会”上,苏青更直言不讳“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此次座谈会参加者大都是当时一些著名的女作家、女诗人,有汪丽玲、吴婴之、张爱玲、潘柳黛、关露、苏青、蓝业珍,还有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别的女作家都说喜欢李清照、朱淑真、陀思妥耶夫斯基、冰心、丁玲等人的作品,只有苏青毫不吝啬对张爱玲的赞美。不过张爱玲也算投桃报李,在说了喜欢李清照、丁玲的初期作品之外,又提到苏青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认为她比任何人都懂得“人类的共同性”,而“那俊洁的表现方法”也让她笔下“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虽然二人的表现很有点互相吹捧之嫌,但实际上张爱玲对苏青的态度颇耐人寻味。
在那篇被无数次引用的文章《我看苏青》中,张爱玲上来就表明自己与苏青其实很少见面,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是很密切的朋友。以张爱玲个性之难以相处而论,很少见面反而是最正常不过的。但张爱玲又这样表明心迹:“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她实际上非常了解苏青,懂得苏青。所以她才明了、也愿意与这个“谋生也谋爱”的女子相提并论。
张爱玲与苏青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苏青可以很直白的痛恨“没有一个男人不好色的”[5],而张爱玲只是委婉的表示“有几个女人是为了她灵魂的美而被爱”。她在《我看苏青》中常常有意无意露出许多二人相似的痕迹来。她们都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身上流淌着贵族血脉的张爱玲“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格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而出身平凡、且遇人不淑以致不得不离婚的苏青也向往着大家族富贵热闹的生活,“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座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然而,这些只能是梦想,在这个生活艰辛、战乱频仍的时代,无论离家出走的张爱玲,还是离婚独自带孩子谋生的苏青,只能“双手擘开生死路”,拼尽全力地生存下去。所以,她们二人都不避讳对金钱的看重,“我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在那个朝不保夕的时代,没有了经济支撑,一切都是烟云。
也许是同为女性作家,她们都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细腻、敏感与多愁。1944年11月11日上午,上海滩有一次紧张的空袭,“全上海死寂”,张爱玲一个人坐在没有电的黑房里,只听见一只钟表滴答滴答走,由从前想到现在,对自己当前所做的努力与成就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幻灭感[6]。苏青也在同一天因空袭而“心上受了伤”,感受到了本国同胞冷酷的心与异国人民的瞧不起[7]。在这个1944年末的同一天,两位当红的女作家都感受到了生之无奈与死之近切。
苏青与张爱玲还都有“小报”情结。张爱玲对小报评价很高,认为它有一种“得人心的机智风趣”,并说自己“从小就喜欢看小报,看了这些年,更有一种亲切感”[8]。甚至在上面提到的空袭中张爱玲还以一种奇异的感觉读着照常送来的一份小报,上面关于大饼、白报纸、暴发户的俏皮话让她感受到生存的气息。而苏青专注于饮食男女的作品本身就颇有“小报”作风,潘柳黛更是曾在1947年12月1日的《力报》上这样评价:“女作家中,写小型报稿子,苏青最有噱头,因为她有‘性’文艺作风”。
尽管谭正璧曾说张爱玲与苏青作品的气氛截然不同,“前者阴沉而后者明爽,所以前者始终是女性的,而后者含有男性的豪放”,“张爱玲在技巧方面始终下着极深的工夫,而苏青却单凭着她天生的聪明吐出她别的女性所不敢吐露的惊人豪语,对于技巧似乎从来不去十分注意”[9],但她们终究可以一起去时装店品头论足,一起在座谈会上相互捧场,一起为同一个男人去求情。
二、“谋生也谋爱”
这个让她们一起去周佛海家里为之求情的男人就是与苏青、张爱玲都有纠葛、且差点与张爱玲“今生今世”的胡兰成。
胡兰成也是《天地》的作者,他与苏青是大同乡,一个是浙江嵊县人,一个是浙江宁波人。《天地》第二期就有胡兰成因苏青第一期的《论言语不通》写的《“言语不通”之故》,此后,胡兰成陆陆续续在《天地》发表了五篇文章,分别是《瓜子壳》(第七、八期合刊,署名“兰成”)、《读了红楼梦》(第九期)、《随笔六则》(第十期)、《乱世文谈》(第十一期)、《张爱玲与左派》(第二十一期)。
胡兰成与张爱玲都曾评价过苏青,且都在关注苏青美不美的问题。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曾这样描述张爱玲对苏青的评价:“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面点有胭脂。’” 胡兰成也认为苏青的脸美。可张爱玲的评价相当缥缈,注重的是感觉,正如她在《我看苏青》中认为“苏青是乱世里盛世的人”,是‘乱世佳人’。”而胡兰成则在《小天地》创刊号《谈谈苏青》中细致形容了苏青的美,她的鼻子、嘴巴,她的鹅蛋脸,她的俊眼修眉,尤其“看书写字的时候,在没有罩子的台灯的生冷的光里,侧面暗着一半,她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与完成,是那样的幽沉的热闹,有如守岁烛旁天竹子的红珠”。假如没有认真地观察过一个人,当写不出如此有质感的文字。难怪常有人以张爱玲的《小团圆》为对照,并结合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怀疑胡兰成与苏青的关系。我们看《今生今世》中胡兰成对于自己有来往的女子,周训德、范秀美、佘爱珍等都有容貌上的细致描写,反而于张爱玲这个最受世人瞩目的女子,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描摹。不过是“她的脸好像一朵开得满满的花,又好像一轮圆得满满的月亮”,无论“花”还是“月”,“满满”似乎都有点俗套,也缺乏美感。至于借用《水浒传》里形容九天玄女的“正大仙容”来表述,与其说是真的因为太过惊心动魄而让胡兰成无法用语言诉说,倒不如说也许张爱玲的才华比容貌更让人惊艳!
然而,苏青的美也只是美而已,《天地》的重要性也并不在于发表了胡兰成的几篇稿件。事实上,正是苏青与《天地》让他结识了张爱玲。在《今生今世》中,胡兰成提到了自己在南京接到苏青寄来的《天地》月刊,提到自己对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的赞赏,细细读了一遍又一遍却仍心有不足。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
且不论胡兰成与苏青此前是否认识,可以确定的是,此处胡兰成的记忆有误。按理来说是不应记错的,让他印象深刻的《封锁》是发表在《天地》1943年11月10日出版的第二期上,而且同期还刊登了他自己的一篇文章。至于那张照片就更不应该记错了,就是这张他后来向张爱玲提到并被赠送的照片刊登在《天地》1944年1月10日出版的第四期,除了张爱玲的照片,还刊登了周作人、周杨淑慧、樊仲云、纪果厂、柳雨生、谭惟翰、周班公的玉照。而且,在这一期中,苏青还特别为张爱玲做了广告:“张爱玲女士学贯中西,曾为本刊二期撰《封锁》一篇,允称近年来中国最佳之短篇小说。在三期刊载之《公寓生活记趣》亦饶有风趣。本期所刊《道路以目》尤逼近西洋杂志文格调,耐人寻味。”
接下来,胡兰成叙述了自己通过苏青联系上张爱玲的经过,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在胡兰成上海的家中“客厅里一坐五小时”,“金童玉女”从此开始了一段上海滩乱世中的传奇。张爱玲的住址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胡兰成则住在大西路美丽园,相隔不远,这两个地方都留下了二人的身影。
1944年8月,胡兰成与张爱玲结为夫妇,此时,他38岁,她24岁。他有妻有妾,是5个孩子的父亲;她虽名满上海滩,却只是信奉爱情至上。胡兰成“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上两句是爱玲撰的,后两句我撰,旁写炎樱为媒证。”此时的张爱玲肯定不会想到,仅仅三个月之后,“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就成了笑话一般。
194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胡兰成对张爱玲说“时局要翻,来日大难,她听了很震动”。11月,胡兰成到武汉接管《大楚报》,在“黄沙盖脸,尸骨不全”的环境里与17岁的见习护士小周相恋了。
1945年3月,胡兰成回到上海。他没有避嫌的与“糊涂得不知道妒忌”的张爱玲说起了小周。5月,胡兰成又回汉阳,“当下我竟是归心似箭,急急渡过汉水”。胡兰成的心完全偏离了张爱玲,此时距离二人“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不过九个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胡兰成不得不变装独自出逃,可就是在惶惶不可终日的逃亡途中,他还拐带了收留他的斯家老爷的寡妾范秀美,“十二月八日到丽水,我们遂结为夫妇之好。”
1946年2月,张爱玲寻到温州,胡兰成的反应是“我一惊,心里即刻不喜,甚至没有感激”。
还记得胡兰成提到的在《天地》上看到的那张照片吗?就在胡兰成提照片的翌日,张爱玲就送给了他,并在背面题了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或许是因为胡兰成在最初见面脱口而出的“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打开了张爱玲的情感之门,写出这样低到尘埃里的句子。
出身贵族、满腹才华的张爱玲以极低的姿态送自己的照片给了比自己大14岁的有妇之夫。然而同样送给胡兰成照片的还有1945年1月的护士小姐周训德。胡兰成要求小周题字,一首隋乐府诗“春江水沉沉,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就出现了。这样平等直白甚至有些挑逗的姿态才更能获得胡兰成的青睐。因为他很快就说“训德,日后你嫁给我”。而张爱玲把姿态摆的很低的题字照片送给胡兰成时,他的反应其实颇令人难堪:“她这送照相,好像吴季札赠剑,依我自己的例来推测,那徐君亦不过是爱悦,却未必有要的意思。张爱玲是知道我喜爱,你既喜爱,我就给了你,我把照相给你,我亦是欢喜的。而我亦只端然地接受,没有神魂颠倒。”
胡兰成曾经说过“平生知己乃在敌人与妇人”,然而他真的了解张爱玲的想法吗?或者说,他了解女人的想法吗?我们知道,胡兰成与张爱玲恋爱的时候并非独身,他认为张爱玲并不在意,甚至“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世上果真有如此大度的女子吗? 胡兰成曾以“一夫一妇原是人伦之正,但亦每有好花开在墙外”为自己开脱,他说张爱玲“糊涂得不知道妒忌”,说小周“真是像三春花事的糊涂”。在胡兰成看来,似乎女人对他的风流韵事都是“糊涂”,这个词的含义真是广泛而具有欺骗意义。
恐怕胡兰成一直都只是一厢情愿。假如张爱玲不会吃醋,就不会在最初往来几天之后,突然写信给胡兰成让他不要再去找她;也就不会在胡兰成告诉她小周的事情后,提到一个外国人愿意与之发生关系并贴补一点小钱;更不会让胡兰成在小周和自己之间做一个选择。然而胡兰成的不肯选择其实已经是做了选择,宁愿让眼前的张爱玲痛苦,也不愿伤害遥远的小周。胡兰成对张爱玲的爱还剩下几分呢?在温州曲折的小巷里,张爱玲第一次责问了胡兰成:“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
现世难以安稳,“岁月”也终究没有“静好”。1947年6月,张爱玲写信给胡兰成诀别,再未相见。
张爱玲其实是明了胡兰成的性格的。但她“凡事像刀截的分明,总不拖泥带水”、“她不会被哄了去陪人歌哭,因为她的感情清到即是理性”。张爱玲终究是一个女子,痛苦时她宁愿有选择的屏蔽,“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10]。她知道“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11]张爱玲并没有比苏青幸运多少。1945年2月27日下午,在《杂志》的邀约下,苏青与张爱玲就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在张爱玲的公寓进行了对谈。在“标准丈夫”的条件上,张爱玲同意苏青的“本性忠厚”、“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等条件之外,又提出“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天真”的张爱玲终于在“有经验”的胡兰成那里爱断情伤。
1945年的正月十五下午,苏青走了之后,张爱玲一个人站在黄昏的阳台上,看着红红的月亮升起来了,想到“‘这是乱世。’……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12]然而,这各人就近的平安亦不可得。张爱玲的去国,苏青的离家,带给她们的都不是幸福的未来。
三、生还是不生?
当今天的我们中许多人面对“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时,无独有偶,六十多年前的《天地》的第七、八期合刊中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其中的“生育问题特辑”。这组特辑共有十篇文章,或主张生育,或主张节育,以收到先后为序,分别是苏青的《救救孩子!》、东方髦只的《不孝有贰》、柳雨生的《节育之难》、张爱玲的《造人》、周越然的《婚姻与生育》、予且的《多子之乐》、亢德的《谈节育》、霜叶的《群小》、谭惟翰的《为父者言》、苏复医师的《节育的理论与方法》。
这组文章中除去苏复以医师的角度深入浅出地阐明节育的理论与方法之外,其余的九篇文章大多以自家为例,通俗易懂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及原因。周越然、予且、亢德、谭惟翰是主张生育的,他们从中国的社会风俗习惯,如讨公婆的欢喜、满足亲友们的期望、巩固家庭的基础以及带给自己的幸福等出发提倡多子之乐;从国家角度看,战争也需要鼓励生育。虽也提到了经济问题,但大都表明养孩子并没有让他们变得更窘迫。
苏青、张爱玲则观点一致,认为节育是必要的,支持的还有东方髦只、柳雨生、霜叶。他们以生计之难、家庭情趣的变易以及过多的生育对母亲造成的摧残为由主张节育,而且从社会、国家角度出发,众多的花柳病、肺结核、心脏病等各类病患不适于养孩子,现今的土地也无法养育这么多的人口。
六十多年过去了,科技有了长足的进步,早已可以成就生活之美;社会也天翻地覆,许多困难早就不再存在。然而生育问题依然是我们的大事。
苏青的《救救孩子!》是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同时附有张爱玲绘的一张非常传神的插图,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眼神忧郁、双唇咬着栏杆。苏青“认为千不应该万不应该的,便是我不该盲目地生了这许多孩子”,她讲述了自己生养四个孩子的经过,二女儿因为送给别人养而被虐待得了童子痨悲惨死去。当她养最后一个男孩子时,“我们夫妇间感情已决裂了。我与我的孩子们生活过得很苦,靠写文章来维持衣食,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于是在一个晚上,我是决定要走了。”作者写了自己与孩子不忍分离时的痛苦,“失去了孩子,我再也不希罕世间上一切!”更不幸的是,她在路上还看见一个早已死去的冰冰冷的婴儿的尸体!“从此以后,我见了路旁的孩尸就心惊肉跳;而路旁多的恰巧是:一包包结结实实的,裹扮得整整齐齐的孩尸。”由自身的经历做比照,文章更有说服力,也更发人深省,因此苏青才会说节制生育“决不是坏字眼,相反地,它们是美丽的,慈悲的,而且合乎正道与常情的”。
苏青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和孩子有关的,即1935年6月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第六十七期发表的《生男与育女》,表明了生男与育女的不同遭遇。此次苏青更是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苦口婆心的劝导,文中有几句话颇让今天的我们心惊:“我很希望国家能早日普遍的设立托儿所,一方面广征有母爱欲求发泄的人来这里担任养育,假如这类女子不太多,则就为薪水而来也不打紧,只要她能尽责,养得儿童长大而健康就好。”
而当时尚未结婚的张爱玲则以冷静的笔调阐述了自己对小孩的尊重与恐惧。“我一向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小孩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 她的文章中有一句话特别容易让今天的我们产生共鸣:“他们不觉得孩子的眼睛的可怕——那么认真的眼睛,像末日审判的时候,天使的眼睛。”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面对天使的眼睛,没有人可以作恶。
不论同意还是反对节育的作者大都提到当时节育方法不给力,以致造成了孩子接二连三的出生。因此,苏复医师的《节育的理论与方法》就水到渠成了。苏青、东方髦只等还倡议设立节育指导所。
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自然不是问题,我们的关注重点也并不在这里。事实上,《天地》的第七、八期合刊于1944年5月1日出版,由此我们很容易判断以当时上海的生存环境来说,无论是主张生育、还是节育,其实都有自己站着得住脚的理由。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彻底沦陷。战争不仅损失了大量人口,也让人们的恐惧和经济压力达到极点。仅以米价而言,按照谭惟翰的回忆“十年前大洋一角可以买一升头号白米”,亢德则提到“今日的米价又是三四千元一石”,而到了苏青在1945年2月1日出版的《天地》第十七期中写的《如何生活下去》一文,则提到“米卖四万多元一石”。通货膨胀之迅速、生活之艰辛可见一斑。而远离政治的《天地》,在苏青的编排中,以这样独特的贴近生活化的视角讨论对时代、对社会有重大意义的话题,亦足以显现出她把握时代脉搏的敏感与迅速,不难理解为什么苏青能在解放后紧跟时代的节奏,写出在当时非常流行的越剧《屈原》以及《宝玉与黛玉》了。
这组文章里最让人吃惊的其实还是张爱玲的文章,她的冷静与睿智都不愧于才女之称。然而,此时的孩子对于张爱玲来说还遥远的很,无论生育还是节育都不成为问题,最多只是以自己对小孩子的感受以及挖掘自己不愉快的童年经历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她一定不会想到许多年后自己的遭遇以及自己或许做过的那个梦。
1955年秋天,张爱玲从香港出发,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驶向不可预知的美国。1956年3月,36岁的张爱玲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遇见了时年65岁的美国作家费迪南•赖雅,二人彼此都有好感。很快,张爱玲发现自己怀有了身孕,赖雅虽然向张爱玲求婚,但表示不要孩子,而张爱玲也同意了赖雅的决定。确实,以当时二人的生活窘境,如果再有一个孩子,真的是雪上加霜。8月14日,两人在纽约举行了婚礼,这次还是炎樱做的伴娘。然而,堕胎是违法的,还是炎樱帮她想办法,最终失掉了这个孩子。在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有这样一段对话:“‘生个小盛也好,’起初汝狄说,也有点迟疑。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13]155或许这真是当年张爱玲不要孩子的真实想法,别说生活窘迫无法养孩子,就是有钱有人带也不要。真相我们已无从追究。然而无论如何,这个选择对于张爱玲来说,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其实都是一种伤害,“女人总是要把命拼上去的”。
这倒是和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对张爱玲的描述一致:“爱玲好像小孩,所以她不喜小孩,小狗小猫她都不近,连对小天使她亦没有好感……中国民间又说小孩的眼睛最净,睡梦里会微笑,是菩萨在教他,而有时无端惊恐,则是他见了不祥不洁了。”或许这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张爱玲为什么会一直对小孩子敬而远之。
在《小团圆》最后,张爱玲写到九莉曾经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不仅有了好几个小孩,而且梦见了微笑的之雍和小木屋,醒来的九莉快乐了很久很久。张爱玲早已是对胡兰成只剩下厌恶的了,然而,根据《小团圆》的自传性,我们知道“之雍”是指的胡兰成。这是一个奇特的梦,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结尾。
生活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14],无论是后悔生了四个孩子的苏青、还是一个孩子也没有的张爱玲,最终都真的成了太平世界里“寄人篱下”的人,都带着“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悲哀离开了人世。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当苏青遇到张爱玲[j].中国图书商报,2001-11-08.
[2] 谭正璧.论苏青与张爱玲[j].风雨谈,1944,(16).
[3] 张爱玲.谈女人[j].天地.1944,(6).
[4] 张爱玲.我看苏青[j].天地.1945,(19).
[5] 苏青.谈男人[j]. 天地.1944,(14).
[6] 张爱玲.我看苏青[j].天地.1945,(19).
[7]苏青.十一月十一日上午[j]. 天地.1945,(15-16).
[8]女作家书简[j],春秋.1944,2(2).
[9]谭正璧. 论苏青与张爱玲[j].风雨谈,1944,(16).
[10] 张爱玲.打人[j]. 天地.1944,(9).
[11] 张爱玲.留情[j].《杂志》1944,14(5).
[12] 张爱玲.我看苏青[j]. 天地.1945.(19).
[13] 张爱玲.小团圆[m].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14] 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1944,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