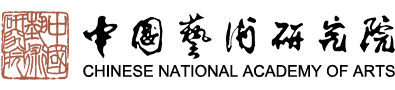田 莉
田莉,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编辑。现为副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著作有《声韵闲情》。参加《中西比较诗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及《中国艺术百科辞典》《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艺术卷曲艺门类等著作的撰稿工作。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明末说唱批评的突破
内容提要:明中叶以后,文人开始高度重视和欣赏民间艺术。说唱以及在说唱基础上发展成熟的白话小说、戏曲、市井民歌等通俗艺术也开始得到文人的肯定,并且备受赞赏。文人们在品赏这些通俗艺术之外,也以多种形式探讨了其中的理论问题和创作问题。明代批评家往往在戏曲批评中以说唱为戏曲的参照对象,揭示出说唱与戏曲的不同所在,从而也阐释出说唱表演的本体性质。如果说明末批评家发现和阐释戏曲表演的本体性是对明中叶戏曲批评理论的突破,那么其戏曲批评文字中对于说唱本体性的理论认识,也是对此前说唱批评的突破。
关键词:明末 说唱 批评 突破
本文发表于《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9期
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的繁荣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同时还带来了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化。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应运而生,颠覆了长期禁锢人们的传统观念,从而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新思潮和审美新风尚。在这一时代思潮与审美风尚的影响下,文人开始高度重视和欣赏民间艺术,说唱以及在说唱基础上发展成熟的白话小说、戏曲、市井民歌等通俗艺术也开始得到文人的肯定,并且备受赞赏。文人们在品赏这些通俗艺术之外,还收集、整理、改编、出版了大量说唱、小说、戏曲作品,同时也以小说序文、评点、笔记以及论著等多种形式探讨了其中的理论问题和创作问题,推动了通俗艺术的新发展。一向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小说、戏曲、说唱,在文人的参与和批评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欢迎。
一 说唱“批评”概念的提出与批评意识
在说唱批评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并使用“批评”概念的人是余象斗。余象斗是明末福建著名书坊双峰堂的主人,著名的书坊刻书家,通俗小说、类书、杂著的编纂者和评点者。在经营世代相传的书坊业的同时,余象斗顺应时代思潮和读者的爱好,编印了大量的通俗作品。经他所编印的书,品种多,数量大,流传广,价值高,其中不乏说唱作品。万历二十年(1592),余象斗刊行《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在印制上首次采用了正文页面分为上评、中图、下文的形式。很显然,在书上标明“批评”的字样,大大突出了“批评”在作品中的地位,同时也使“批评”这一概念首次进入说唱话语之中,并使之成为说唱批评的自觉观念。不仅如此,余象斗还把“批评”的字样与“全像”并列使用,把万历以来小说刊刻中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为一体,使作品文本、作品图像、作品批评成为一个整体,既显示出余氏刊刻小说的一个基本形态,又可以把批评的观念推向读者,使读者能够领会批评的重要作用。
此后,余象斗刊刻的《水浒志传评林》,同样在书名上把“评”标示出来,使“批评”成为余象斗刊刻小说的特殊标志之一。该书最值得重视的是,余象斗在评点中删改了原作,开创了在书的每一页做一栏简短评语的小说评点方式,奠定了“改”与“评”相结合的中国小说评点的基本格局,突出了批评家的地位,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评点家,特别是清代小说评点家金圣叹。
当然,小说评点的形式早在宋代就已问世,但明代小说评点是以一种融批评、鉴赏、理论建构、文本增饰和形式修订于一体的综合活动。它以通俗小说为评点对象,不仅表现出批评家对于通俗作品的欣赏和赞美,而且批评家的评点之词和删改对于更多的读者是一种讲解、释疑和引导。由于作品、图像和评点结合于图书的同一页,所以更加方便读者深入地品味作品,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当然,由于余象斗是以书坊刻书商人的身份来评点小说,带有比较强的商业性,评论比较简单,见解比较平庸,因此余象斗对于说唱批评的贡献,主要还在于提出“批评”的概念和确立批评的格局。但他作为中国古代说唱批评史上一位有重要影响的批评家,毫无疑问功不可没。
与余象斗追求商业性功利目的的评点不同,明代文人在关注民间各种通俗艺术的同时,表现出具有时代精神的批评意识,并且不断推动明代整个社会与文化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李开先是明代文人中较早把目光转向民间的批评家,他从民间歌诗发现民间艺术的意义,提出重视民间通俗艺术价值的批评观念。接着是李贽从哲学意义上关注业已产生广泛影响的说唱艺术,主张把“童心”作为感受和评价艺术的基础,强调追求精神的快慰和主体意志的张扬,不仅为说唱批评注入了新的艺术观念,而且对晚明通俗艺术批评具有深刻的影响。
李贽是明末重要的思想家,也是说唱批评史暨小说批评史上重要的批评家。在李贽众多的评点中,相当多的部分是针对说唱作品或在说唱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小说的批评。现存署名李贽的《水浒传》的评点本,一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刻一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为万历三十九年前后袁无涯刻一百二十回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尽管其中容与堂本有托名之说,两种本子作为民间艺人说书基础上形成的小说评点,对《水浒传》的思想和艺术都有精彩的分析,因此突出了评点方式的优越性,并成就了评点方式成为说唱批评史上的批评方式之一。
不仅如此,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叙》中称《水浒传》为作者的“发愤之作”,进一步阐释了“童心”“真心”是艺术创作的根本。对于李贽来说,“童心”亦即感性情欲的自然表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作品才是“天下之至文”。文统观念以文体为文学判断的重要标准,是从尊体论优劣,不能真正认识民间通俗艺术的价值。因此李贽把“童心”作为至文妙文的标准,进一步把“至文”、“妙文”作为评价艺术的重要概念。李贽指出,天下之至文不在于引经据典,惟古是从,也不在于所产生的年代,更与文体无关。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只要有“童心”和“真心”,“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因此稗官小说、传奇、杂剧这类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也可因其有“童心”而成为天下之至文。“童心”者,直见“本心”和“真心”,不受“道理闻见”的束缚,不被“虚文”、“皮毛”、“浮理”所遮蔽,而直见“神骨”和“人情”的文心。李贽指出:“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就是“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 在他看来,反抗封建礼教的《西厢》、《拜月》为童心之作,《水浒传》是童心之作,而被一些人标榜为全忠全孝的《琵琶记》则是“似真非真”的作品。因此李贽特别提倡自然,重视发自“童心”的艺术作品。
“童心”之作是自然地表达,艺术表现的“自然”源自于“童心”的感发。在李贽看来,“童心”的感发是一种痛快淋漓的宣泄: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由此可见,只有有感而发,而非无病呻吟的表达才是真情,才有可能创作出感人的佳作。
李贽完全背离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和”原则,把情与理看作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百姓日用之迩言”出自民众之“童心”,有可取之处。李贽认为:“好察迩言”,“则得本心”。所谓“迩言”,李贽指的是“街谈巷议,俚言野语,至鄙至俗,极浅极近,上人所不道,君子所不乐闻者”,实际上就是下层百姓日常生活用语。在他看来,:“善言即在乎迩言之中”,“唯以迩言为善,则凡非迩言者必不善”;“迩言”不待教而后能,“是谓天成,是谓众巧,迩言之所以为妙也” 。这就是说,街谈巷语,俚言野语,表达本心的感情,绝假纯真,与《六经》、《语》、《孟》无涉,即出自于“童心之言”。如果用“迩言”表达日常生活,也是一种自然天性的流露。由此可见,李贽的“童心”说与“迩言”论,表现出要求革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表现出新的思想和生活的文学观念,也打破了正统文化的权威。因此可以说,李贽批评的新观念开了时代文艺之先河,提高了民间各种通俗艺术的艺术表现力和文化地位,推动了明中叶以后文艺新思潮以及说唱艺术的新发展。
晚明文人金圣叹改编《水浒传》等,一方面将与民间说唱和戏曲相关的通俗艺术经典化,提高说书文本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使其不再仅是说书的经典,也是文学的经典。另一方面,才子书和奇书之说与文人的小说评点,也是晚明审美风尚的反映,它肯定了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的世俗生活意义。晚明文人袁于令将当时的评话改编成小说《隋史遗文》,同时主张艺术就要“惊俚耳”、“快俗人” ,要适应民众的审美情趣,透露出一种自觉的说唱创作理念。
明中叶以后,特别是晚明,文人对包括说唱在内的俗体艺术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积极参与,一方面推动了俗体艺术的盛行,树立了中国通俗小说的典范,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具有新时代意义的社会文化思潮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当时的文人们从观念上改变了以往对俗体艺术的传统观念,身体力行参与俗体艺术的创作和批评,提升了一大批俗体艺术作品的品位,也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文人将其艺术趣味投入到世俗生活,对日常生活中的俗事俗物赋予雅趣。在时代风气与审美风尚影响中的民间说唱,与文人气息一起释放的是改编的说唱小说、模拟创作的白话小说以及经评点推出的才子书和奇书。在明代文人与民间艺人的互动中,形成了以雅化俗和以俗化雅的双向审美价值取向。这不仅使戏曲、白话小说等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促进了说唱文本化,出现了拟话本,而且使各种说唱方式进一步成熟和发展,使从前的说话人变成了说书人,并且开始了说书由书场至案头、再由案头至书场的转变过程。
从说唱和戏曲在文人观念中的改变,可以看出晚明之际俗体对尊体的有力冲击,是从对人的发现和对人的肯定开始的。正是有了对人的发现和对民间的发现,才大大加强了对俗体文艺的重视和文人对俗体文艺的批评。冯梦龙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称为“明代四大奇书”,张竹坡点评《金瓶梅》“第一奇书”,金圣叹择取《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作为“六才子书”等等,显示出通俗小说评价体系发生了重要的观念转变。
明中叶以后艺术发展的新融合和新风尚,显然是市民阶层和文人之间双向交融的结果,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市民的审美趣味和世俗格调与文人的品位交相融汇,从而改变了文艺批评对通俗艺术的传统评价。
二 明代说唱批评的突破
李开先的民歌批评,开启了晚明文人通俗艺术批评之风,使通俗艺术得到了应有的评价。所谓文人批评,是文人身份的批评者以文人立场、文人情趣、文人艺术观念为基础对于艺术的认识和判断,其核心是文人的艺术精神及其价值观念。因此晚明之际文人通俗艺术批评的意识,在表达时代精神追求的同时,往往突破了长期形成的文统观念。
首先是尊体意识的突破。
在正统文化观念中,历来以“辨体”为先,重视文体形态的界限和高下之分。从“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来看,不同的文体之间有着尊卑、雅俗的等级之分。尊体,即诗出《诗经》、文出《尚书》,均为有经典依据而谱牒堂堂的文体。历来以诗文为代表的雅文学都被视为正统正宗,诗、文为尊体。相比之下的说唱与小说、戏曲等等,都被视为鄙野之言,淫邪之辞,出无经典,查无依据,纯系俗体文学,故不在正宗范围,辨体为卑。
在儒家观念的支配下,历来以小说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充其量也只是“史”的附庸。班固《汉书•艺文志》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班固从三个方面奠定了传统小说观念。首先,小说讲的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类的琐事,“盖出于稗官”;“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盖亦史官之末事” ,因此“小说”是“史”的附庸,相对于正宗的经史一类大道而言,小说属于“小道”。其次,小说虽属“小道”,但“小道”亦有“可观”之处,应“亦弗灭”。再次,“小说家合残丛小语” ,小说毕竟是“刍荛狂夫之议”,所以就不能对属于“小道”性质的小说津津乐道,应该谨慎地保持距离。很显然,传统史学观念支配下的“小说观”与艺术的文体和叙事关系不大,必然束缚小说理论的发展。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二千年的时间里,虽然对小说的理解有一定变化,但一直以小说为“史”、为 “小道”,小说观念基本上没有改变。
与此相一致的是,正统文人把说唱艺术同样视为“小道”。在他们的眼中,说唱艺人犹如“倡优下贱,得为后饰” ,只是为了满足人主愉悦和欢心。因此艺人所表演的说唱故事,一方面和传统史学观念中所说的小说相同,讲“街谈巷语,道听涂说”及“史官之末事”,讲“刍荛狂夫之议”,属于“小道”;另一方面和正统观念中所描述的曲艺相近,乃小小技术,若医卜之属” 。说唱虽“小道可观”,但采用的是順其所好的进言方式,更可谓“小技”与“小道”。“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 ,那么与正统相对的异端小道则不正。因此正统观念中的说唱不仅属于体卑的“小道”“小技”,也表明说唱艺术体卑与异端的性质。
尊体意识决定了说唱和小说的出身谱牒微贱,致使说唱、小说文体向来不能入尊体之列。在尊体意识的影响下,艺术价值判断首先关注文体(形式),而不是着眼于艺术本身的叙事及其表现力(内容)。因此长期以来说唱和小说一直不受文人学士的重视。针对这种现状,李贽鲜明地提出: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
论艺术优劣不能只注意文体,文体不能完全反映艺术本身的优劣,谱牒的尊卑也不能决定艺术成就的高低。在李贽看来,稗官小说也好,传奇也好,诗文、时文也好,都只是艺术形态不同而已,没有尊卑的差别,都一样可以成为天下之“至文”、“妙文”,同样也都可以成为劣文。所以评价艺术优劣的着眼点不在于艺术的形态,不在于文体尊卑,而在于艺术本身是否是“至文”、“妙文”。李贽不以尊卑论文体,强调从艺术本身来评价艺术,主张以“至文”、“妙文”的观念取代文体尊卑的观念,首先针对的就是传统文体尊卑观念。长期以来,文体观念一直把俗体文学视为体卑,史学观念一直把俗体文学视为小道异端,体卑和“小道”的意识一直影响着对俗体文学的价值判断和对俗体文学地位的肯定。李贽破除文体尊卑观念,表明文体并不能作为文学价值判断的标准。对于李贽来说,文学价值判断的标准是“童心”,是作品所表现出的“文心”。事实上,李贽在评论作品时的确是不遗余力地鼓吹“俗体”。正是从作品所表现的“文心”和“童心”来衡量作品,而且往往把所谓体卑的小说、传奇和说唱看得比正统文人的诗文还高。
李贽提出不以尊卑论文体、以童心评至文妙文的批评观,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异端,突破了文统批评的传统藩篱。在李贽的影响下,俗体文学广泛引起文人的重视,扭转了长期以来对俗体的评价倾向。
以尊卑论文体,一向是文论的基本意识。但明中叶以后批评家的艺术观念开始具有鲜明的世俗倾向。当然,对俗体的批评,一方面欣赏俗体的气质,一方面仍然以诗文为尊体,在观念上把俗体与诗文经史相提并论。
其一,小说与经史并列。有明一代文人对小说戏曲等俗体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的肯定,往往与《六经》、《史记》一类经史并提。在批评观念里,似乎俗体文学的地位,需要表明出身谱牒为正宗;俗体文学的价值,需要经史“大道”来提升。实际上,这种从小说与经史比较来肯定小说的特殊价值,还是传统小说观念和史学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明中叶李梦阳第一次将《西厢记》与《离骚》并列。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等一批文人又将《水浒》与《史记》并称。李开先《词谑》云:“《水浒传》委曲详尽,《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水浒传》的问世,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反响。李开先充分肯定它的价值,第一个把小说与《史记》相提并论,表明小说的叙事艺术具有独特的价值。汪道昆(托名天都外臣)把《水浒传》与《史记》并提:
纪载有章,烦简有则,发凡起例,不染易于。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夫《史记》上国武库,甲仗森然,安可枚举。而其所最称犀利者,则无如巨鹿破秦,鸿门张楚,高祖还沛,长卿如邛,范菜之倾,仪秦之辩,张陈之隙,田窦之争,卫霍之勋,朱郭之侠,与夫四豪之交,三杰之酸,十吏之酷。诸吕七国之乱亡,《货殖》、《滑稽》之琐屑,真千秋绝调矣!《传》中警策,往往似之。
汪道昆以艺术的眼光准确把握《史记》传记文学的特点,用《史记》叙事记人最光彩的篇章彰显《水浒传》的精彩,即在于肯定《水浒传》“往往似之”的艺术表现力。汪道昆赞叹《水浒传》的叙事和描写艺术完全可以和《史记》相匹,从而充分肯定《水浒传》和《史记》一样,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
至晚明时期,批评家为肯定小说的价值,为提高小说的地位,不仅把小说与《史记》并提,而且与《六经》并提。袁宏道把词、曲、小说与《庄》、《骚》、《史》、《汉》并提,把《水浒传》、《金瓶梅》视为“逸典”。在他看来,《六经》和《史记》的艺术性其实都不如《水浒传》。袁宏道在《听朱生说〈水浒传〉》中说:
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
在袁宏道的眼中,《水浒》尽管属于俗文学,却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特别是说唱艺人朱生表演的《水浒》,更增加了生动性和艺术表现力。相比之下,在正宗的雅文学观念中的《六经》虽是经典,却未必有《水浒传》那样的艺术表现力。袁宏道对朱生说唱《水浒》的评价,除了《水浒》文本之外,还包括说唱艺人的现场表演。不论从小说还是从说唱而言,袁宏道都把《水浒》置于《六经》之上。他不仅肯定了《水浒》以及朱生说唱《水浒》的成就,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小说的价值,并突出了小说应有的地位,可以说已经大胆地突破了《六经》诸史为尊的正统观念。
对于俗体的认识,冯梦龙显然更加具有明确的把握:“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 通俗既是俗体的基本性质,同时具有入耳的基本特征。因此俗体与尊体的不同在于,“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冯梦龙充分意识到俗体的文化价值,而且大力收集民歌、编辑整理改进俗体作品,推进了俗体批评在操作意义上的展开。
其二,曲体与诗并论。说唱体以曲体演唱,虽与曲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明人关于曲体的认识,往往包含着说唱体。为了提高曲体的地位,明初曲论家以强烈的“尊体”意识,提出“曲亦诗”的观点,认为曲与诗同宗同源。朱有燉认为曲就是诗,同诗一样可以兴观群怨,抒情言志。王世貞认为词家为诗之流,是变风之滥觞。何良俊也如是说歌曲乃诗之流别。臧懋循同样说诗词曲源本出于一。这种“诗曲一体”的认识在明代的曲论著作中比比皆是。明人认为曲是从诗词演化而来,曲与诗词同宗同源,所以一改视曲为“小道”的偏见,大大提高了曲的地位。但曲毕竟是有别于诗词的艺术样式,具有自身的艺术特征。明初曲论家出于“尊体”的考虑,或多或少忽略了曲与诗的不同,也是一种历史选择的需要。明中叶以后,李开先、徐渭、王骥德等曲论家从语言和精神品质两个方面厘出曲与诗所具有的不同艺术特性,指出曲与诗原是两肠。
与争取小说地位和曲体地位的批评不同的是,李贽的批评鲜明地提出要破除文体有尊卑的俗念。在晚明文学批评之中,李贽的批判最为深刻,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冲击也最为强烈。他在肯定小说戏曲俗体文学的同时,批判的矛头直指传统文体观念,力求从根本上突破正统的艺术观和史学观的束缚,使小说戏曲等俗体文学从“小道”和体卑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李贽反对以文体尊卑论俗体,提出“童心说”,把源自于本心的自然文字作为至文妙文。如果从正统艺术观来看,李贽显然是异端。但这是时代新精神的反映和时代艺术观念的新声。在李贽的影响下,晚明文人提倡、评点、议论俚野稗官竟成为一时风气,一举改变了艺术以文体论尊卑的传统。李贽不仅在说唱批评史上第一次解决了艺术形式的尊卑地位问题,使说唱一类“俗体”艺术可以与诗文一类的“正体”艺术相提并论,而且推动了晚明艺术的新发展,使说唱艺术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
其三,明确了以情为本的创作原则。
说唱这种形式突出表现社会中下层人的普通生活和情感,是一种深得平民喜爱的娱乐方式。明代批评家主要从曲体角度着眼,发现了民间俗体艺术的真实价值,在肯定之余,也充满了欣赏赞誉之情,从而体现出明中叶以后的审美趋向。
(1)以情为本的创作原则,强调曲体本源在于民间。徐渭的“民俗之谣”论述具有代表性:
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东西南北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行,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
又有何良俊的见地:
古乐之亡久矣,虽音律亦不传。今所存者惟词曲,亦只是淫哇之声,但不可废耳。盖当天地剖判之初,气机一动,即有元声。凡宣八风,鼓万籁,皆是物也。故乐九变而天神降、地祗出,则亦岂细故哉!
徐渭与何良俊的说唱发生说,强调的是曲体的“声”部系统,而不在文辞之意义。尤其徐渭明确指出“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是对“乐府”本质最切实的揭示。就是说,“民俗之谣”的“天机自动”,正是曲唱之声发生的根本来源。因此即使“淫哇之声”,也与“天机”相应,亦不可废。“天机自动”,表明曲体源于民间,民间曲是文人曲的母体,因此传统的雅正艺术观再也不能作为判断民间艺术的最高标准。
(2)以情为本的创作原则认为俗体艺术本性在“情真”。“天机自动”,必然表现出一种情真,这是俗体艺术突出的特色。明代批评家偏重情理对立,特别强调“情”在文学中的意义,正是在于把情作为一种天机和自然的本性表现。“真诗乃在民间” ,这是当时一个最响亮的提法。明代批评家看到民间俗体艺术表现出的自然率真之情与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更发现了自然率真之诗对于人情的张扬。因此在他们眼中,所谓“真诗”,即“情真”之诗,即出自于民间表达民间真情的民歌。李开先是较早表明这种态度的批评家,他说:
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自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
忧而词衰,乐而词亵,此古今同情也。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锁南枝〕],一则商调,一则越调。商,伤也:越,悦也:时可考见矣。二词哗于市井,虽儿女初学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艳亵狎,不堪入耳,其声则然矣,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友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以感人也。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三百篇》太半采风者归奏,予谓今古同情者,此也。
民间的小曲虽小,却包含大情;里巷的俗曲虽俗,却人人明白易懂。李开先揭示出民间曲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真,一方面表现在“直出肺肝”的情真,一方面表现在“不加雕刻”的直白,因此民间曲歌能够“以其情尤足以感人”。李开先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指出了民歌的本体特性,从“真”的文学价值功能上肯定了一向为正统文化所鄙薄的民间俗体艺术。
袁宏道也同样特别重视民歌的情真,而且把民歌的情真作为人性的一种表现: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虽则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在袁宏道看来,出自于民间无名之辈的真诗之所以能够情真,在于不受任何戒律的束缚,率性而发,尽情表达。袁宏道从民歌小曲的“任性而发”,看到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因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可见袁宏道对民间真诗的肯定,建立在对人性积极肯定的基础上,同时也正由于民间真诗表达的是真情实感,因此能得到明代一批批评家的赞赏。
冯梦龙(1574-1646),受李贽影响较深,肯定“民间性情之响”,并提出“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即以山歌所发真情,揭露贩卖封建礼教伪药的诗文。冯氏辑有话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民歌集《挂枝儿》、《山歌》,拟民歌《夹竹桃》,散曲集《太霞新奏》,笔记《古今谈慨》等。他毕生从事通俗文学及俗曲的搜集、整理工作,成绩卓著。在《山歌•序》中他对俗曲的论述也旗帜鲜明,颇有见地: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籍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材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
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自唐人用以取士,而诗入于套,六朝用以见才,而诗入于艰,宋人用于讲学,而诗入于腐。而从来性情之郁,不得不变而之词曲。……今日之曲,又将为昔日之诗,词肤调乱,而不足以达人之性情,势必再变而之“红粉莲”、“打枣竿”!
在冯梦龙看来,诗歌应该是人们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民间山歌表达真情,就是“性情之响”;民间山歌没有任何所求,但其“情真而不可废”。可见冯梦龙肯定的是俗体艺术表现的人之心灵。小曲虽“俚甚”,都是“男女私情谱”,但其“情真”就是真正的“诗”。而且,世上“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山歌的“真情”可以“发名教之伪药”。不仅如此,也正是在对于人心真情表现的基础上,冯梦龙在肯定民间山歌的同时,又将民间山歌与经典的传统诗文对立起来,甚至称经典诗文为“假诗文”,不仅突出了民间山歌作为“性情之响”的审美价值,而且明确显示出对于经典正统文学的颠覆意识。由此可见,晚明的批评家实际上是把“情真”作为曲体文学的本质,从而大大强调了“情真”的意义。因此民间艺人说唱才能够得到文人批评的关注与审美价值的认可。
(3)以情为本的创作原则提倡俗体艺术明白易晓的文风。李开先在提出“真诗在民间”的同时,指出真诗“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实际上揭示的是民间小曲的体性特点,而且俗体除了内容的通俗,最重要的就是语言表达的明白易懂。因此明代批评家尽管从不同的俗体艺术来认识俗体的本性,但都把语言的明白易懂作为体性之本。陈继儒《唐书演义序》云:“演义,以通俗为义者也。”雉衡山人《东西两晋演义序》云:“好事者聚取而演之,以通俗喻人,名曰演义。”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进一步刻意宣扬通俗话语的创作:“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矣。义不必演,则此书亦不必作矣。”徐渭是较早从本体意识上探讨曲之本质属性的,其《南词叙录》云:
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辏补成篇。吾意: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也?
徐渭第一次提到“得体”这一概念,表明他具有明确的本体意识。在这里,他以“得体”来把握俗体,规范了“得体”的概念内涵:其一从演唱角度来说,“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其二从语言角度讲,语言“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也?”艺术产生于人心的感发情动,但不同于正统诗文的是,曲与民歌生存于民间,语言的表现以“奴、童、妇、女皆喻”为本,明白易晓为俗体“得体”之所在。因此徐渭主张曲唱语言宁可鄙俗一点,也不能晦涩,实际上强调的仍然是把易晓的通俗语言作为俗体的根本所在。继徐渭之后,明代批评家主要是从语言特性来把握俗体艺术,显然首先肯定了俗体之本在于语言之俗。
当然,一味强调语言的通俗并不能保障创作的趣味和艺术品位,但是强调通俗语言的创作,显然在艺术观念上肯定了说唱语言的通俗性质。随着嘉靖年间第一部长篇通俗小说《三国演义》问世后关于历史演义文体性质的讨论,新的小说观念逐步建立起来,使民间说唱尤其是说书艺术得以更新艺术观念,并且有新的发展。
(4)以情为本的创作原则,认识到曲之本性与游戏相同。在曲的本性问题上,明代又有一些批评家提出游戏说。从曲体体卑的意义上来说,曲乃小道末技,那么大道意义上的“载道”与“言志”,就不是曲的本性。沈德符云:“填词出才人余技,本游戏笔墨间耳。” 徐复祚云:“文章巨擘,羽翼大雅,黼黻王酋,正业之外,游戏为此。” “词曲,金元小技耳,上之不能博功名,次复不能图显利,拾文人唾弃之余,供酒间谑浪之具,不过无聊之计,借以磨岁耳,何关世事!” 所谓“游戏笔墨”、“酒间谑浪”、“借以磨岁”之语,尽管表达的也是一种所思所想所感,但和“诗言志”相比较,却并不属于正统、严肃的大道之言,多顺其所好的戏谑之辞,往往沉湎于男女之事。无论从题材到文字,曲之本性即在游戏。李开先的《词谑》不论词曲可以言志,王世贞的《曲藻》也不谈曲可言志,对他们来说,词曲属于卑体,是小道小技,但作为一种游戏,亦可获得文学的旨趣。
总而言之,明代批评家尽管从不同的角度阐释曲体本性的问题,但都能够表明说唱艺术与俗体在艺术精神上具有一定的共同性,都是来自于民间性情的“情真”之作,是民众生活和情感的表现。文人对于说唱本性的发现,反映出时代审美思潮的趋向,表明明中叶以后的艺术发展以俗体艺术为主。
其四,艺术发展的俗体化是一种发展趋向。
随着明中叶以后文艺世俗化思潮的深入,明代艺术发展的俗体化趋向愈加突出。一批自觉的批评家不仅发现俗体艺术中的情真天机,而且把俗体化趋向作为时代精神和时代艺术的标志。王思任《王季重十种•杂序》云:“一代之言,皆一代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 袁宏道《与江进之》云:“古之不能为今者也,势也。其简也,明也,整也,流丽痛快也,文之变也。夫岂不能为繁,为乱,为艰,为晦,然已简安用繁?已整安用乱?已明安用晦?已流丽痛快安用聱牙之语、艰深之辞?……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 还有徐渭《又题昆仑奴杂剧后》强调:“语人要紧处,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杂一毫糠衣,真本色。……点石成金者,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
晚明文人对于文体代嬗的清醒认识,一方面注意到俗体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中心化,语言的通俗和文体的通俗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文学自身表达的要求,同时还是社会文学消费主流群体的要求。另一方面则肯定俗体艺术表达的的精神价值。晚明审美时尚主流转进入了一个肯定世俗生活、张扬个人享乐的新潮,俗体艺术表达发展的趋势就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因此,晚明之际俗体深入社会文化生活,与中国文人传统艺术既对峙又形成雅俗互通的时代风尚。俗体以俗化雅,在改变社会文化生活和日常娱乐生活的同时,丰富文人的艺术观念,不断推动社会发展的世俗化。文人则不断重申以雅化俗,关注和参与俗体创作和批评,不仅促进俗体技艺的丰富和艺术化,而且从艺术精神上肯定了俗体对于人性和个性的张扬。俗体事实上改变了中国古代雅文化一体的文化结构,构成民众艺术与文人艺术的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三 说唱表演的批评论
在宋代出现“说唱”一词以后,说唱体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得到不断发展,同时也不断得到批评家的关注。虽然说唱表演一直是批评家重视的问题,但是从说唱是表演艺术的意义上认识说唱的本质,在说唱批评中并不多。直到明代,批评家开始关注叙事性曲体即戏曲的本体问题,才能在曲体批评中看到对于说唱本体的基本认识。
第一,说唱的表演是说法现身。程羽文《盛明杂剧序》云:
盖才人韵士,其牢骚、抑郁、啼号、愤激之情,与夫慷慨、流连、谈谐、笑谑之态,拂拂于指尖而津津乐于笔底,不能直写而曲摹之,不能庄语而戏喻之者也。……可兴、可观、可惩、可劝,此才人韵士以游戏作佛事,现身而为说法者也。
在程羽文看来,戏曲属于现身说法。戏曲以抒情表现为主,“牢骚、抑郁、啼号、愤激之情”都可以在戏曲中抒发,“慷慨、流连、谈谐、笑谑之态”也可以在戏曲中得到表现。但是戏曲的抒情不同于生活中的发泄,艺术表现必须创造出与现实的距离感、超越感和自由感,从而在戏曲中表现出一种游戏的性质。对于艺术的游戏性质,胡应麟指出,传奇“亡往而非戏也” ,“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或奇士洽人搜罗寓外” ;谢肇淛称戏文为“游戏三昧之笔” ;以至清人李调元说:“剧者何?戏也。” 以此看来,程羽文所谓现身说法,实际上即于戏中说法。“现身而为说法”,语出《楞严经》卷六,观世音菩萨言:“我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慧远《大乘义章》卷十九云:“佛随众生现种种形,或人或天,或龙天鬼。如是一切,同世色像,不为佛形,名为化身。” 佛根据不同的对象而现出不同的身形,做出不同的样态,都是根据宣讲佛法的需要,不断变换自身的角色。具体而言,佛、菩萨一方面始终保持讲经人的身份,用通俗的事例和通俗的语言宣讲佛法,一方面随时根据讲经需要变换身份,以不同众生形象现身,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说佛法。显然宣讲佛经的方式是“说法现身”,与程羽文所谓戏曲“现身说法”并不完全相同。戏曲的现身说法,虽然只把现身与说法的词位顺序调整,但实际上改变了艺术的表现方式。也就是说,戏曲之旨不在于说法,而在于现身,在于现身的表情根据题材的表现需要,或庄重严正,或滑稽调笑,以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状忠孝而神钦;状奸佞而色骇;状困窶而心如灰;载荣显而肠似火;状蝉脱羽化,飘飘有凌云之思;状玉窃香偷,逐逐随波之荡。
然而讲经则以说法为目的,现身在于说法,为了说法的需要可以不断进入角色,又不断走出角色。说唱继承了讲经的艺术传统,坚持艺术表现上的说法现身,与戏曲明显不同。程羽文《盛明杂剧序》提出戏曲的表现特征,虽没有明显地直接论及说唱,但从戏曲的角度涉及到说唱表演的本体问题。
第二,说唱是一种专业性强的表演技能。艺人表演的说唱一向讲求入里耳,在讲故事说人物的同时,形成丰富的艺术手法,得到明代文人说唱的重视。首先,说唱表演通常以曲代言以曲传情,或者是以曲牌连套方式说唱,或者是以短曲抒情方式演唱,一般选自于既成的音乐体裁。固定的曲牌,地方性音乐调性,诗赞体韵律,不仅丰富说唱故事的生动性,更容易加强唱曲的感染力和传播性。通常所谓“旧瓶装新酒”指的就是用程式化的音乐唱曲,用程式化的讲故事套路把点使活。
其次,说唱艺人注重在历史叙述与虚构相结合的结构中,敷衍故事与描绘人物。至晚明,说唱批评对俗体叙事特征的把握基本上是一种共识,就是意识到俗体叙事突破了实录观念,主张在虚实之间敷衍创作。冯梦龙明确描述到:“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可废乎? ” 同样金圣叹对《水浒》叙事方式的提出“因文生事”的观念,即强调所谓“生”就是虚构和创造。俗体叙事并不拘泥于史书记载的人物和事件去讲述真人真事,往往在史书框架中,大量虚构敷衍。因此冯梦龙看到俗体叙事具有“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 的重大感染力。于是俗体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同时讲世俗故事的叙事方式和审美态度也不断在培育民间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
明代说唱伎艺不断丰富和完善,俗体叙事的虚构观念进一步影响俗体的发展。一方面文人将艺人重要的说唱改编加工出版成为文本作品,并且按照艺人表演是叙事方式创作出新的拟话本小说,是对时尚说书表演的追随与肯定。说书表演在当时艺术发展的影响力和审美习惯的导向,构成晚明文化发展的一种新风尚。另一方面艺人将经过文人删订整理加工的话本作为说唱的底本,从前的说话人转变为说书人,确立了民间说唱成为与文人艺术以及官方主流文化共存的文化格局。
第三,说唱的表演是在场上进行。清人陈乃乾对宋元以至明清说书艺术的表演特点概括得非常精到:
吾国宋元之际,市井间每有演说话者,演说古今惊听之事。杂以诨语,以博笑噱;托之因果,以寓劝惩,大抵与今之说书者相似。惟昔人以话为主,今人以书为主。今之说书人弹唱《玉蜻蜓》、《珍珠塔》等,皆以前人已撰成之小说为依据。而穿插演述之。昔之说话人则各运匠心,随时生发,惟各守其家数师承而已。书贾或取说话人所说者,刻成书本,是为某种平话。如今之编京剧谱者,盖出自伶人口传,非伶人依谱而成也。
场上说书的表演特征非常突出:说书人既要调笑,又要讲教化之词,其实并不容易。所以说书人采用的办法是,在讲故事时善用诙谐语言吸引听众,注意迎合听众的趣味。这段话对说唱表演的艺术特点概括得非常到位。显而易见,艺人为了吸引听众,会在作品内容之中掺杂很多其它因素来增强表演效果。
王骥德《曲律》对戏曲本体的探讨,以最明确的阐释把说唱本体性作为戏曲本体认识的比较对象,是最早体现说唱表演本体性质的批评理论。其《曲律》杂论三十九上云:
古之优人,第以谐谑滑稽供人主喜笑,未有并曲与白而歌舞登场如今之戏子者;又皆优人自造科套,非如今日习现成本子,俟主人拣择,而日日此伎俩也。如优孟、优旃、后唐庄宗,以迨宋之靖康、绍兴,史籍所记,不过“葬马”、“漆城”、“李天下”、“公冶长”、“二圣环”等谐语而已。即金章宗时,董解元所为《西厢记》,亦第是一人倚弦索以唱,而间以说白。至元而始有剧戏,如今之所搬演者是。此窍由天地开辟以来,不知越几百千万年,俟夷狄主中华,而于是诸词人一时林立,始称作者之圣,呜呼异哉!
王骥德在这里对戏曲本体的认识和理解,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他对于说唱本体的阐释,在中国古代说唱批评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他把戏曲与说唱作为相互参照的艺术,肯定了两者在发展史上的密切联系。其二,区分了戏曲与说唱的不同,并将两者加以比较,在确立戏曲概念的同时,也揭示出说唱本体的表演性质。王骥德强调戏曲有两个内在因素,一是“搬演”,即舞台性,要“并曲与白而歌舞登场”,强调戏曲是综合的表演艺术;二是“现成本子”,即文学性,戏曲演出要有“现成本子”,即戏曲剧本。这两点是戏曲最为本质的特征,显示出王骥德对戏曲本质特征的精确体认。王骥德主张戏曲要“可演可传”,就是强调戏曲的舞台性和文学性。他认为“词藻工,句意妙”而“不谐里耳”的“案头之书,已落第二义”。在舞台性和文学性之间,王骥德更看重戏曲的舞台性和戏曲的演出效果,但也认为不能放弃戏曲的文学性。
至于说唱,王骥德的描述是:“以谐谑滑稽供人主喜笑,未有并曲与白而歌舞登场”,“自造科套,非如今日习现成本子”,“不过‘葬马’、‘漆城’、‘李天下’、‘公冶长’、‘二圣环’等谐语而已”,“董解元所为《西厢记》,亦第是一人倚弦索以唱,而间以说白”。显而易见,王骥德在关于戏曲本体的阐释中,多半的文字是描述说唱,但透露出王骥德对说唱并不欣赏。在这里,王骥德从表演的目的、登场表演的形式和风格、演出文本几个方面区分了戏曲与说唱的不同。相对于戏曲的特性,说唱表演是以一个人表演为主,有说有唱;登场之前有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