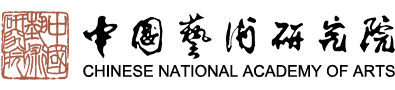陈文璟
陈文璟,艺术管理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书画评论家、著名策展人。
图像的消亡与数字时代的中国绘画
图像概念是一个符号学概念,沟通的是人类精神世界。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那么,图像就是由一人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是我们由此可以窥视其精神世界的桥梁。所以,图像研究的终极目的不应成为图像构成的技术性分析,而应着眼于图像阐释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才是构成其意义之网的关键。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这里的“我”不再是“动物”似的个体存在,可以虚化为人类精神契合了自然与生命之后的一种真实体验,这种体验要有益于人性的最终完善。当然,“我”也可以用中国文化中的“道”来替代,这样的图像学阐释更符合中国哲学的品位,也更加适合阐释中国绘画的图像样式。
本文发表于《爱尚美术》杂志,2018年4月。
一 图像的消亡与时代变迁
我所认知的图像概念应该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沟通的是人类精神世界。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那么,图像就是由一人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是我们由此可以窥视其精神世界的桥梁。所以,图像研究的终极目的不应成为图像构成的技术性分析,而应着眼于图像阐释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毕竟,这个价值观才是构成其意义之网的关键。另外,我觉得这个定义还可以做进一步的阐释,就是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这里的“我”不再是“动物”似的个体存在,可以虚化为人类精神契合了自然与生命之后的一种真实体验,这种体验要有益于人性的最终完善。当然,“我”也可以用中国文化中的“道”来替代,只是无中生有的“道”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存在,玄之又玄。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虽然这样的图像学阐释更符合中国哲学的品位,也更加适合阐释中国绘画这个具有玄学意味的图像样式,但我们还是形而下地了解下当前绘画样式的变化与技术进步产生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由此界定这个时代的中国绘画应该具有的什么样的形态。
中国文化绵延发展了近五千年,图像作为人类文明最初的沟通方式在原始人时代就开始出现,这一点毋庸置疑,已经为中外艺术史家所认可。例如最著名的半坡人的1955年陕西省西安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形象奇特、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纵使没有巫祭的图腾信仰因素,至少也体现出家长希望孩子在另一个世界吃饱饭的意识。事死如事生,此世间和彼世间对中国人来说,两者之间的关联从来都是不即不离,而非截然对立的。沟通两者之间的桥梁除了通过祭祀巫使这样的专业人士,普通人显然也可以借助于真诚的心意通过图像来建立。再如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楚帛画,《升天图》和《人物龙凤图》,前者体现的是彼世间的景象,后者体现的是此世间往彼世间的依仗。许多学者对此都进行了详尽的解读,不一一列举,但无论哪一种阐释,都不能避开图像本身具有的沟通两个世间的作用。之后就是在汉末三国两晋时期的中国绘画正式登台亮相,自此中国绘画摆脱了现实的束缚而具有了自己的独立世界,成为彼世间的一部分,但却附属于此世间。郭向注《庄子》说:“故与世同波而不自失,则虽游于世俗而泯然无迹,岂必使汝惊哉!”(《庄子·天地》)泯然众人又自有乾坤,不求奇搞怪博取眼球,讲究和光同尘,这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它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绘画大师。同时,也因为这些大师的薪火相传,虽然经过上千年的延续发展,中国绘画的样式也多种多样,但其指导精神,也就是沟通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使之平衡个体精神面貌的功用却从来未曾有过大的变动。所以,作为图像符号存在的中国绘画不应仅仅是一种外向的关系或者利益诉求,更多源自于人类阐释内在体验的需要。基于此,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客观的图像形式虽然可以说是一种几乎永恒的存在,但具体到绘画领域,若其指示失去了引导、完善人类内向体验提升的价值,图像图式本身即可被认定为已经死亡。例如:现在以数字手段高清仿制出的古代艺术品我们只会将其定义为产品,或者商品,绝对不会将其定义为艺术品。艺术究竟不是一种实验科学,不能靠着研究光谱和色彩构成、形式排列等规律创作就大功告成,它还需要创作者注入其对自然世界、社会人生的种种体验,包括情感、情绪和文化沉淀等等,甚至还需要来自于受众的体验和阐释,内外结合,才可以最终成就艺术品的价值。
我当然不是在否定图像形式构成的重要性,毕竟任何绘画种类均不能脱离图像形式的构建,这是其作为造型艺术的本质属性。中国传统绘画也不能例外。我们研读画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绘画形式的变化脉络。从最初的线描到董源的雨点皴,然后是宋代的斧劈皴,米家皴、元代的披麻皴,牛毛皴等等。明清画家则在精神内涵上丰富着中国绘画的艺术形式,直到近代,中国绘画领域内的大家大多在某一领域取得了一些与前人有所不同的进步。可以这么说,历代在绘画技法上有所突破的画家都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这也侧面说明了图像形式构成的重要性。然而,明清以降,画家在具体实践中的经验表明,要确切地了解图像,获得艺术上的进步,关注点不能是图像,而应是图像所以成为图像的开始。比如明初画派流弊,清初四王图式的僵化,都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过去图像的消亡。清初的王石谷将画道不彰归咎于画派流弊,说:“洎乎近世,风趋益下,习俗愈卑,而支派之说起。文进、小仙以来,而浙派不可易矣。”他认为画家应“代为师承,各标高誉,未闻衍其余绪,沿其波流,如子久之苍浑,云林之澹寂,仲圭之渊劲,叔明之深秀,虽同趋北苑,而变化悬殊,此所以为百世之宗而无弊”,这个观念正确,却很难落地。民国初的陈独秀号召进行“美术革命”,革除“四王”以来的中国画流弊,说:“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陈独秀 《美术革命》)与王石谷温和的文化态度相反,陈独秀在文化动荡的时代采用的文化突破手段是激烈的,因为传统的文化阵地实在牢固,不激烈也不行。他说:“谭叫天的京调,王石谷的山水,是北京城里人的两大迷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许人说半句不好的。”(陈独秀 《美术革命》)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虽然号召他人采用“革命”这样的激烈手段,陈独秀家里所藏的几百张王石谷的画却没有烧掉销毁的记录,应该是通过他们家的画廊出售了。
是以形式僵化固然不可取,形式创新也未必名副其实,形式永远具有欺骗性。经过上百年的振荡,我们现在提倡恢复传统文化,传统绘画自然也首当其冲。但是,如果仅仅是恢复旧有的艺术样式,显然是错误的。郑玄《毛诗 正义》:“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中国绘画与中国诗歌有天然的关系,所以此义一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绘画的文化内涵,即体悟自然世界的规律,表达自己的胸怀情绪,坚持读书人应有的道德操守。所以古人绘画,讲究画外之功。唐张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唐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明董其昌说:“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明 董其昌 《画旨》)于是,就中国绘画而言,毕竟图像构成不能止于构成,它所隐喻的文化指示还需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义”,即所谓的“成教化,劝人伦”,这是我们的绘画传承。当然,过于执着于“大义”,那么图像就会僵化,乃至失去活力;过于执着于图式,那么图像就会单调,乃至失去价值。无论是失去活力,还是失去价值,这样的图像,可以说已经死亡。
二 技术进步与内心超越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 原道中》说:“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也就是说,在孔子之前,政教合一,所以读书人只需按照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做事,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孔子之后,政教分离,读书人有了自由思想的权利,可以依照自己的秉性去理解事物,并以自己的方式去改变自我和世界。虽然因此各执一词,以自己的道为是,以他人的道为非,是非纷然,却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大势。其实这是庄子在《天下篇》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引申阐释。
所谓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在庄子而言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而我们以后来者的眼光审视,则他们出于一个令人非常振奋的时代,毕竟那是一个技术突破,文化升华的时代。“突破”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不破不立”是一个文明得以蜕变升级的机会。更何况随着生产技术的变化,生产关系也出现了变化,读书人从此自旧有的桎梏中脱身而出,获得了选择此世间或者彼世间的选择权。因此才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从容,有了陶宏景的“山中何所有,岭上白云多”的自信,有了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自强不息,有了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坦然淡定。所以,庄子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在那个天崩地裂的大时代,没有放弃对内心超越的认同感,更没有放弃超越内心的种种努力。韩愈说:“道其所道。”(韩愈 《原道》)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道,但也尊重其他人选择的权利,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其实是一个“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化环境。毕竟大家都是围绕着“道”这个中国文化本体展开讨论,始终没有脱离文化正常完善的轨迹。所以,这一次的文化“突破”最终导致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态度,也确实逐渐产生了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肌体。余英时曾说:“西方学者曾指出,中国古代的超越的突破最不激烈。”(余英时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激烈”的原文是least radical,我觉得解释为“激进”更加明确。因为庄子那个时代的文化突破是一种在固有的文化价值上的完善,是本质的升华,不是颠覆性的革命。
历史证明,每一个大时代的变化,都源自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然后才是生产关系的革新,最终导致人类社会的更迭。西方社会对于技术的变化有种天然的热情,所以他们的文化突破很激烈,甚至有时候变得太激进,所以高潮迭起。而中国的封建时代特别长,文化的发展一直比较平缓和稳定。但是,近代机器大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列强短期内迅速成为世界霸主,他们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不仅贩卖黑奴,挑起种族冲突,更悍然发动战争,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天下大势谁也没有办法避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个稳定繁荣的国家迅速堕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技术的引进导致了文化的“突破”来得非常突然,人们几乎没有消化的时间,就又来到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
所以,我十分理解陈独秀那一代文人迫切希望引进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以改变中国的心情。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荡时代,他们大概一方面有感于受制于技术落后,屡战屡败的国势危情,另一方面也源自于他们内心的精神力量已经无法超越现实世界,也就说彼世间于此世间的人来说越来越远,过去沟通所用的桥梁显然是年久失修,已经不适合普通人体会那种两个世间“不即不离”的亲密。很遗憾,我觉得可能是清朝政府三百年的统治,也可能是近两千年的封建时代令读书人感到了厌倦,这一次他们竟然自觉地放弃了选择的权利,采取了完全附庸于西方文化体系的方式,显然是太激进了。现在想想,那一代人纵使不想重视两个世间的亲密感,也不应该把刀相向,斩断两者之间的关联,使两者成为对立方,导致之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开始白热化,从而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中国绘画自然也就随之发生的巨大变化。
陈寅恪曾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又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育,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神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在中国绘画领域,画家们是否有“善应付此环境”而致“富贵荣显,身泰名遂”的情况呢?这且放下不讨论,但国画大师傅抱石说过:““国画家世界观和艺术观的问题,也是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问题”“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你不同,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傅抱石 《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这就将本属于彼世间的绘画强硬地牵扯到此世间,将亲密的关联重置为必然的斗争。所以,这个时代的文化环境上已经出现了异变,不仅仅是画道不彰的问题,根本就是颠覆画道的时代。虽然那个时代也培养了层出不穷的画家,承担着中国绘画的延续,但是很显然,效果甚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小山终于说了一句真心话:“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了。”(李小山 《当代中国画之我见》)这句话体现出他对内心是否能超越现实的绝望。他说:“中国画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在技术处理上(追求’意境’所采用的形式化的艺术手段)不断完善、在绘画观念(审美经验)上不断缩小的历史。”(同上)虽然李小山认为的“绘画观念不断缩小”是错误的,但不排除他说的绘画现象确实存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创作确实穷途末路了,因为他们过于注重形式构成,过于依赖技术进步,试图通过改变中国绘画的材料,解构中国绘画的文化内涵来获得新时代的绘画图像。或者说,他们都忘记了,在技术突破的时代,我们人类需要在内心超越方面也取得相应的突破,这样才可以平衡人类社会的存在价值。李小山认为“绘画观念在逐渐变小”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绘画是人生的体验,它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是否完善,是否纯粹的问题。倪瓒对于人生的体验非常纯粹,所以,尽管他的绘画里面常常空无一人,却足以跨越时空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
就技术突破而言,近三十年来才是中国绘画需要认真面对的时代。之前因为数字摄影、印刷技术的桎梏,无法将视觉经验直接传达给后人,只能通过文字来阐释其主观的视觉,这本是无可奈何的举措,但也避免了后人的牵强附会。不过,奈何后人曲解附会能力之强,缘木求鱼之下,遂成一篇篇长篇大论,洋洋洒洒,动则万字以阐释。再到后来的人不明其谬误所在,一味附庸风雅,所以只能随之起舞,以之为确论,于是又是洋洋洒洒数万言。东晋殷浩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晋 刘义庆 《世说新语 排调》)信乎其然也。当前的学术环境普遍西方标准化,这已经是确定的现实,根本不必讳言。其他领域我也不熟悉,单就中国绘画来说,以素描速写为基础,以西方图像构成等理论来阐释和发展,无异于竹篮打水。尽管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促生了摄影、印刷技术,令艺术品的复制摆脱了人类的情感注入,对于传统绘画经典的复述更加完整、本真和权威。这显然有利于后人学习古代的图式,更加利于新图式的产生。但是,这种缺乏了人类灵魂注入的技术复制同样也正式拉开了人类图像艺术消亡的序幕。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将艺术作品中人类的精神注入称之为“光韵”,而光韵的消逝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普遍存在,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前景,他悲观地总结说:“在对艺术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复制技术把所有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两方面的进程导致了传统的大崩溃。”(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iii节。)事实上,这不是指示艺术传统样式的崩溃,而是图像图式的光韵的消逝,也是人类在艺术领域的创造力,或者是精神力的消亡。没有“光韵”图式创新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今天看似有更多的图像图式可以提供我们去欣赏,但“千人一面”的现象十分突出,这与其本身缺乏足够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有关。
三 数字时代的中国绘画与改变世界
在数字化的信息时代,消费文化主导的文化运动突破了原有的西方学术文化体系,于是也在颠覆着近百年图像创作的一些标准。毕竟中国逐渐富强,人民生活水平上升,民族文化的自信也逐渐加强,中国人究竟还是愿意在绘画层面选择中国绘画,不仅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情怀,更有那种对两个世间的亲密感具有的天然亲切。一方面因为西方列强力量减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信息数字化让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子,人们开始更加注重相互之间的尊重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体系。为此,人们强调文化的多样性,要求进行大数据的收集,试图将图像的一切都进行符号化、碎片化处理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材料和细节的完整性、本真性,强调“本土化”的重要性。这当然跟国家生产技术的进步有很大关系,虽然碎片化信息等等对原有的中国绘画的哲学理论构成了冲击,但对中国画家在内向超越方面也不是一无是处。首先就是一个信息的完整系统化。无论资料是如何被碎片化,但真正取舍使用资料的人是可以将其复原的。也就是说,一旦画家拥有了画道的审美情怀,他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历代大师的笔记心得,历代的经典作品,他可以十分便利地完善自己的画道体系。其次,信息化的便利可以让画家迅速厘清文化泡沫。时代发展速度快,文化泡沫不可避免,诸多人等也免不了浑水摸鱼。只要画家有一个定见,保持一定的耐心,那么妖魔鬼怪很快就会露出原形。信息化造成了一个公共信息空间,每个身陷其中的人很难确保私人空间的隐秘,是以若想在这个时代成名,还是要谨言慎行,否则所有的荣华富贵很可能就会成为虚妄。而那些内向超越了此世界的人,无欲则刚,刚近仁,故可以非常坦诚地面对这个时代。
所以,尽管数字化时代的中国绘画也受到了消费文化的冲击,也因之出现了一些图式空洞柔弱的艺术典型,但这却非中国绘画的末日,更不是我们认识图像艺术的终点,甚至这将是我们进行图像重置的契机。一般来说,人类永远不可能放弃精神追求的完善,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中国绘画必将再次成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品。无论东西,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总会不断地赋予图像一些强大且具有冲击力的概念,以此而阐释所有图像带给我们的问题,这些概念给予我们一种强烈的暗示,就是它们将解决所有的重大问题,澄清图像所有隐含的意义。然而,当我们熟识这类概念之后,就会逐渐发现这种概念的局限性。于是,我们一方面会在某种范围内继续使用这样的概念来解决响应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还会不断地完善它,或者完善我们自己的认知,从而能达到一个新的升华。《大学》上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荀子》曰:“凡论者,贵有辩合,有符验。”(荀子 《荀子 说符》)是以,我们需要研究图像所以成为艺术的根本,沿着那一条自古而来的脉络将其重新界定,乃至进行艺术的复兴,文化的复兴。因为,文化复兴和自强永远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作为消费文化的主体,引导中国文化走向本民族固有的精神归宿,不是像落叶归根那样自然吗?
具体到中国绘画领域,绘画的继承和发展确实得益于不断地艺术品复制。晋朝谢赫的“六法”一直作为中国绘画的审美标准,其中有一条就是”传移模写“,就涉及到了艺术品的复制。艺术术语是”传写“,常言说的是”临摹“。不过,这种复制并非完全的技术复制,还有精神传统的体会和完善。唐代出现的双钩技术大概是比较早的临摹复制方式,主要是保持原图的本真性和完整性,甚至在一些原迹损毁,需要画家修补的地方都专门进行标识。但是,这种方式都临摹只能是最初级的,尚不属于传承的核心。中国绘画的传移模写传承的是文化审美观。通过样式地反复学习,体会创作者的精神状态和文化认识,从中汲取营养,培养自己对笔墨线条规律的认知,从而最终实现图像上的自我完善,完成艺术个体的形式创新。所以,目前所有的复制技术还影响不了中国绘画的传统,反而有助于更多的爱好者可以接触到绘画经典,画家也能更加方便地学习古代样式。
那么中国绘画的画道该如何去把握呢?古贤说:无心恰恰用。这真正是中国艺术的不传之密。不传并非因为保守,而是传授的只能是知识和图示,境界却只能个人去体悟。有人会问:无心怎么用?艺术创作本身并非为了艺术而存在,而是为了“成教化、助人伦”的现实目的,创作者并没有考虑图像的形式构成,笔墨线条的结实厚重等等形式问题,但出来的作品偏偏就是内容形式的完美统一。反而那些一意追求形式上的突破,追求受众的意见的作品达不到前者主客观的完美契合。俗话说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这样的状态。道家思想提倡“有”成于“无”,所以,成教化,就是成就绘画的教化功能;助人伦,就是维护中国文化固有的礼仪秩序,这两者都建立在“无欲”之上才有效果。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来说,这就是在改变世界。一般来说,中国绘画对世界改变来自于画家对内向的文化突破,是一种道德上的由己及人式的潜移默化。孔子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 阳货》)改变世界的努力不是形式主义,更不是打着道德旗帜去要求别人,而是我们自己以“仁义道德”为其内在根本去创作艺术品。他还说过:“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论语 颜回》)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的认识体系,直接充实完善着中国绘画的“写意”传统。
最后,为了更好地理解东西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他设想了一个有着长长的通道与外部世界相连的地穴,一组囚徒背对着出口,四肢被套上了枷锁,头颈也无法转动,则终其一生,他们只能看着对面墙壁上被火光投射的影子,当然还有人们的嘈杂声。柏拉图说,这样一来,囚徒们一生中所感觉或经验到的唯一实在就是这些影子和回声。对他们来说,他们能够谈论的“现实”以及对“现实”的经验都来于此。现在,有一个囚徒来到了外面的世界,认识到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则他有两个选择,要么他接受现实,要么回到洞穴中。然而,他的经历对其他囚徒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搞选举,他一定会落选,虽然他掌握了真理,结果一样。在这个叙述中,我觉得柏拉图真正秉承了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将文化的突破定义为外在的超越,彼时间代表着真理,此世间代表着洞穴的隐喻,所以他的兴趣点在理想国,一个完全与此世间脱离、截然不同的王国,那里有绝对的真理,人们只需要绝对的服从(柏拉图 《理想国》第七卷)。他这样的条件设计太过于“理想”化,一旦统治者固执己见,很容易走向极端政治。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 《孟子 尽心上》)事实上,这是将精神和肉体对立化的二元论,或许对理解西方艺术有所帮助,但对中国传统绘画来说,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谁缚汝?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剥夺你自由思考和自由选择的权力!这是自孔夫子之后中国文人的情怀核心。由此,北宋人张载才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一直觉得这是中国读书人尝试改变世界的座右铭。中国画家若不想自己隔离在文化体系之外,那么这也将是他们修养养性的最终目标。虽然他们的手段可能更偏向于道家的“和光同尘式”的文化超越。
同样的光影照壁,北宋学者苏东坡也做过类似的实验,他说:“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北宋苏轼 《传神记》)在苏东坡的语境下,见者的信息是完整的,主体也没有被束缚得连头也不能动,一切都在轻松自然地状态下完成。所以,对于绘画,苏东坡得出了“君子寓意于物,不可留意于物”(北宋 苏轼 《宝绘堂记》)的结论。或许在逻辑思辨上苏东坡的实验显得有些粗略,但谁愿意去做那个被捆在柱子上,头也不能稍微转动,还得终其一生都在洞穴中生活,信息极端闭塞的人呢?
在一个繁荣和平的时代,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数字信息化十分便利的时代,我们还是趁此机会,至少为中国绘画艺术的繁荣作出一点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