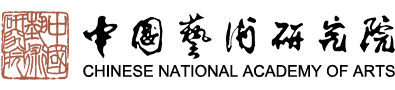朱京生
朱京生,北京市人,首师大书法本科班毕业。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近现代研究室主任,京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陈半丁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画院传统绘画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专业特长:中国近现代艺术史研究,侧重考察与口述史,兼国画、书法、篆刻创作。著《陈半丁》《<白石老人自述>索隐》《被颠倒的历史——国立北平艺专三教授罢教与国画论战事件考察与研究》等,著作、论文多次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科研成果评奖中获。
陈半丁三题
本文“陈半丁与海派的渊源”从金石与翰墨两个角度切入,钩沉陈半丁与任伯年、吴昌硕、蒲华等海派巨擘的关系,有填补画史空白意义;“责任与担当”论述其在京派历史上的领袖作用,特别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抵制以及新中国美术研究与创作机制方面贡献的战略意义;“陈派绘画的审美特点”主要谈陈半丁 “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合凝雅俗审美倾向,合辙于一个泱泱大国蒸蒸日上的意象,可以说它是艺术的民族和国家形象。
本文发表于《中华书画家》杂志,2018年1月
一.陈半丁与海派的渊源
金石缘
1895年,表叔吴隐从绍兴带陈半丁来到上海虹口,在严信厚的“小长庐馆”以拓图章(《七家印谱》)、刻碑、楹联为业,这是陈半丁最早与金石结缘。吴隐印宗“浙派”,《七家印谱》虽被认为是伪谱,但里面所收“浙派”印家的作品不乏佳制,耳濡目染的影响是免不掉的。奇怪的是,目前所见陈半丁的篆刻里面,竟然毫无“浙派”的影子。后来,严家聘请吴昌硕、蒲华等海上名家,半丁与他们相见,颇得厚爱,时时得深切指使,所以真正将陈半丁领进印学之门,并且登堂入室的是吴昌硕。陈半丁《手书自传》云:“十九岁去上海,得蒲作英先生之助介往同里任伯年先生指示(一说得到吴昌硕帮助介绍,见下文。待考),不久又遇吴昌硕先生之同情,旦夕得同室深研有十年之久,获益匪浅。”[ 陈半丁《手书自传》,现藏中国美术馆]《陈年》,刻于1898年,吴昌硕为篆印稿,半丁刻成。半丁自刻边款曰:“二字缶老为余篆也,戊戌十月半丁记。”这是所见缶翁与半丁第一方合作之印,也是至今为止,所见陈半丁最早的一方篆刻作品。此印用刀略显稚弱,学印时间应当不会很长。值得注意的是,这方印章 “吴篆陈刻”的模式,或许是缶翁教授篆刻的独特方法。
1900年,叶舟(为铭)为陈半丁仿汉官铸印刻《陈年长寿》,四年后他与 丁仁、 王禔、吴隐创建了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西泠印社;缶翁次子吴涵年廿八游宦江西,前後凡九载,其间为半丁刻《静山》,款曰:“静老令涵刻于滁上”。这种同辈印家之间的交谊,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有待挖掘。
1904年吴昌硕函约陈半丁到苏州的家中作伴,遂与缶翁朝夕相处,得其口传心授,篆刻水平勇猛精进。本年所作《陈年》,中规中矩,刀法爽健饱满,颇有神采,较六年前之作已有了天壤之别;同年所刻《无所事室》,虽然在边款中称是“用汉人刻法”,但已是一派吴氏作风,得缶翁“钝刀硬入”之法,说明对印之古朴浑茫之意已有深刻领悟,否则不会有如此神似缶翁之作。次年所刻《陈年》《半丁》两面印,刀法上已趋爽劲成熟,水平与1898年已不可同日而语。
1906年,陈半丁来到北京。1910年2月,金城为陈半丁刊一名印《年》,款曰:“庚戌二月巩伯”。 巩伯即金城金北楼,也工篆刻,是北方艺坛的广大教主,有多部印谱存世,仅此前就辑有《藕庐丙午印存》六册、《藕庐丁未印存》六册、《庐戊申印存》四册、《藕庐己酉印存》四册等,也是北方的篆刻名家。 颇为有趣的是,另一款为“年自改作”。可见,“吴门”十年的熏陶感染与修炼,陈半丁此时的手眼功夫已然居于北楼之上。抑或金城当年力邀半丁北上,不单单只是欣赏半丁的绘画。
1910年夏,吴昌硕应邀来京。在京盘桓的数月时间,吴昌硕为弟子半丁刊《抱一轩》《山阴陈年》《静(晴)山》《我无为》《半丁》等印,陈半丁在《静山》一印的边款中刻道:“苦先生刻。庚午冬初,缶老北来,为年刻十余印,此其一也。静山今号半丁。”继续“吴篆陈刻”的教学模式,与半丁合作《有鱼》《半丁》《静山无恙》《陈》《山阴道上人》《静山》等印,边款中往往曰:“庚戌秋缶道人篆,半丁自作”“聋叟篆,半丁刻”“昌硕半丁合作此印”“静山三十后始号半丁,缶翁篆,半丁刻”等等,半丁又在《山阴陈年》缶翁边款“苍老”后面记曰:“吴缶老刻印与让之同工异曲,此后则不可多得矣。”这应该是和缶翁分手以后的一种感叹。总之,吴昌硕此行不仅对陈半丁的篆刻乃至书画起到进一步的筑基和推动作用,而且两人共同书写的篆刻史上这段鲜为人知的佳话,应该视为二十世纪篆刻史上的一次“南风北渐”,值得深入探讨。
1915年,陈半丁刻《半翁》一印,水平已经达到与吴昌硕乱真的程度,自己也忍不住在边款里感叹:“半丁治印,近吴缶老”。 有了缶翁这样一个高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心手便追随而去。
此后,陈半丁在缶翁的基础上上溯吴让之,且更加广泛深入地师法秦汉及先秦古玺之长,迎来了新变,渐成自家之法。在北方,他与陈师曾并称为“二陈”。寿石工在1923年《题印谱》中列举完明清诸大家之后,又说:“并世同辈,若陈师曾、陈半丁……胥于印学深造有得。”此实为确当之评。无独有偶,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中,谓陈半丁“初为杭州西泠印社主人吴石潜之学徒,后以石潜之介拜缶翁为师,绘画刻印,无不神似……余见其绘画中,自刻诸印,无一不佳,甚至有超过乃师吴昌硕者……”[ 53—54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百年印家之中,能当得这样评价的印家是不多的。
翰墨缘
“小长芦馆”的严信厚是海上众多画家的赞助人,严家聘请了吴昌硕、蒲华等海上著名书画家,陈半丁在这里与这些名家交往,有幸得到一段翰墨因缘。当时缶翁正值壮年,精力旺盛,对半丁经常予指点,后又领其到任伯年(颐)处补习翎毛、人物。陈半丁与任伯年是同乡,又经吴昌硕的推荐,因此一见如故,得其教诲,获益不浅,可惜不足一年,任伯年便去世了。
六十二年后谈起这位昔日的老师,陈半丁仍然滔滔不绝:“任伯年学画开头学双勾,后来人物学陈老莲。任渭长学陈老莲做到了‘炉火纯青’,而任伯年学陈老莲则一变其法,比任谓长出格。所谓入范围而能出范围,有自家面目,能独树一帜。他作画思想快,构思巧;下笔如风,顿挫有法。会用套笔,一笔当四五笔用。画人物,能从脚上画起;画美人,有时眸子点在眼皮上,远看却特别有神。当时上海的国画界都很佩服他,朋友中甚至有人称他为‘画圣’……他讲究结构,用色舒服,用笔巧妙,这是同时代画家所赶不上的。”[ 陈半丁《任伯年和他的画》,载《美术》,1957(5)]虽然从学不及一年,但任伯年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极为深刻,任氏的风格在陈半丁的人物和翎毛作品中也时有流露。
1906年,时任宁波会馆董事的严子均,来信邀尚在苏州吴昌硕家中的陈半丁回上海作画。其时上海宁波会馆正要修整,内中不少任伯年的作品都已破烂,需要复制,于是陈半丁便回沪在严家精心临摹任伯年的作品。可见在当时陈半丁是不二人选。但其水平从后来陈半丁两幅拟任伯年的《梧桐白凤图》中能窥见一斑,一幅是1909年作留以自家补壁,另一幅为次年应金城之嘱而作,技法都极为精湛,与故宫博物院藏的任氏原作相比,形神毕肖。
有趣的是,半丁也颇得另一位海上名家蒲华的喜爱。他对蒲华有这样的描述:“……只有一位蒲华,约有八十余岁,妻子早死,又无儿女。每早在茶馆内洗脸吃茶点,常约我去吃饭陪伴,饭后各自回去。此老一身还算健康,就是始终不愿说出自己真实年龄。能画竹石等,善书好诗,对我独厚。”[ 北京画院藏《陈半丁档案·自传》]《风尘三侠》,带有明显任伯年风格,创作时间应该在1895年到1906年之间,款识由蒲华代书,曰: “风尘三侠,静山画,作英题。”这样一个小长芦馆当年交往的痕迹,可视为为那段画史留下的一个弥足珍贵的注脚。
当然,“海派”画家中,在陈半丁心中地位最高影响最深的还是吴昌硕。至少到1920年代中期以前,陈半丁的书法、花卉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吴氏风格。正如启功先生所说:“老先生(指陈半丁)平生最佩服吴昌硕先生,平时谈艺,没有不提‘缶老’的……真如古人所谓‘寤寐受业’了。”有不少作品能见证他们非同一般的关系。1904年,缶翁尝为半丁临石涛《墨荷》一幅,题诗曰:“白菡萏花承露景,野慈姑叶刺菭衣。香风消受梦初觉,邻水人家破竹扉。静山仁兄嗜余泼墨画,为拟清湘老人,时甲辰冬十一月,同客沪。昌硕吴俊卿并句。”1906年,陈半丁受缶翁之嘱临摹了一幅《吴昌硕先考妣图》,吴昌硕十分满意,为此后吴家每年春节祭祖所用。
天津美院教授王振德先生,1960年代就以学生的身份,拜访过半丁老人。他在《日记》记录了一则趣事:一次,齐白石从琉璃厂买了一幅吴昌硕的画,请陈半丁鉴定。陈一看,这不对!这不是我当年的代笔吗?[ 参见2004年王振德先生在“陈半丁与二十世纪北京画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及2007年笔者对王振德先生的访谈笔录]可知陈半丁在1906年离开上海时的绘画水平,已经达到能够替老师代笔的程度了,以致能让齐白石先生都打眼。
由于金城的赏识和邀请,陈半丁1906年来到北京,开始以卖画为生。最初三年颇感吃力,于是在1910年请吴昌硕来京襄助。是年缶老到京,“下榻友人张弁群(查客)家遍游名胜古迹,极诗酒之雅,诙谐之乐。”[ 参见吴长邺:《我的祖父吴昌硕》,306页,上海书店,1997]并为半丁在琉璃厂两家纸店撰写润例,予以推荐,曰:“半丁画润。整张:四尺四两,五尺六两,六尺八两,八尺十二两。条幅:视整纸减半。册页、纨折扇:每件一两。刻印:每字一两,砚铭:另议。半丁旧友,性嗜古,能刻画,写花卉、人物直追宋元,近写罗汉变幻百出,在佛法中可称无上妙谛,求者履盈户外,为定润目如右。庚午长夏吴俊卿。”(陈半丁后人藏)如果结合上文提及吴昌硕为半丁刻印以及合作的情况看,这推荐力度相当不小了。所以陈半丁在《手书自传》中又说:“邀吴缶老来北京盘桓数月,与吴观岱、贺履之、陈师曾相处互助,较前(有)起色……”[ 陈半丁《手书自传》,中国美术馆藏]可见陈半丁在北京卖画的局面有所改观,直接得力于恩师的助阵,及与吴、贺、陈之间的互助。
1911年陈半丁从北京返乡,至1913年重来。先在上海逗留,看望已定居上海的恩师。吴昌硕为半丁临《散鬲铭》相赠,并题曰:“散鬲铭字体遒劲古穆,读虞椒释文,以鬲中地名皆蜀邑,定为蜀器。吴愙斋也以此说为然。兹见拓本,系赵惠父藏物,为半丁先生临末后一段,幸教我。癸丑六月,吴昌硕时年政七十。”1915年,吴昌硕又作书法条幅,为半丁题诗两首,其一《画菊》:雨后东篱野色寒,骚人常把落英餐。朱门酒肉熏天臭,讌赏黄花当牡丹。其二《画松》:“僵卧有如龙蛻骨,后凋不比凤栖梧,岁寒矫矫凌霜雪,肯受秦封作大夫。”款曰:“半丁老兄嘱录近作”。同时又赠《墨梅》一幅,可见师生感情的深厚。
在《陈半丁自编年表》1924年一栏中,显示“师至日”三字,说明这一年吴昌硕还有一趟北京之行,可惜目前尚未看到于此相关的作品和相关研究。这次京华聚首,或许是半丁与恩师的最后一次接触,也未可知。
陈半丁与吴昌硕、任伯年之外的海上各家,也有着广泛的接触,大凡高邕之、吴穀祥、吴石仙、金吉石、金瞎牛、吴伯涛、胡菊邻、杨伯润、陆廉夫、倪墨耕、黄山寿、顾麟士、费余伯、黄山寿诸辈,都有所请益,由此 “方知笔情墨趣,用意立法,超逸枯润与气味神韵,虚灵巧拙之奥……”[ 陈半丁《手书自传》,中国美术馆藏]海上十年的艺术滋养,为后来在北京的发展打下基础。
总之,作为“南风北渐”的重要画家和后来的“京派”领袖人物,陈半丁的人生和艺术已经日渐被学术界和社会所重视,但其早期很深的“海派”背景和渊源,在“海派”的相关研究中或多或少、或有意或无意的被忽略了。
二.责任与担当
在陈半丁九十五年的人生历程中,由一个绍兴孤儿成为“海派”弟子和“海派”后劲,继而以书画印“三绝”之功北上京华,成为 “南风北渐”的重要人物;又在金城、陈师曾去世之后,于1927年被选为“中国画学研究会”副会长,开始跻身“京派”的领袖行列 。此间他与会长周肇祥一同改组画会,继续倡导“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绘画宗旨,为培养画学新人,发展京派绘画起到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周肇祥由于与日伪的关系,在政治上失去地位,影响力逐渐下降乃,陈半丁的作用得以凸显。新中国成立后,陈半丁迎来了他艺术创作的春天和人生最为的辉煌阶段。他被聘为中央文史馆官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尼友好协会会员,出任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长等职,有了更大的责任与担当。
陈半丁在画坛的从善如流,表现在生活与艺术的诸多方面。
早在1917年,齐白石为避家乡匪乱,只身来到北京,想以卖画、治印为生。无奈画作“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心中不免落寞。所幸,这一年齐白石结识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两个贵人——陈师曾和陈半丁。今天,凡提及齐白石的“衰年变法”,陈师曾的作用几乎无人不知,而对于陈半丁在里面的贡献就不大了解了。其实,王振德先生1960年代的《日记》里,记录下了半丁老人有关的谈话。他说:“齐白石刚来北京时,画卖不好,也卖不贵。我劝他学学缶老昌硕,他听了。齐白石这个人很知言,能取得后来的成绩不是偶然的。”[ 转自2004年王振德先生在“陈半丁与二十世纪北京画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及2007年笔者对王振德先生的访谈笔录]不经意间的一句“我劝他学学缶老昌硕”,道出了20世纪艺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齐白石之所以能成为画坛巨匠,放弃八大山人冷逸的画风而改学“海派”吴昌硕的绘画是其成功的关键,这就是著名的“衰年变法”。《日记》中还记载了陈半丁对齐白石篆刻的指点,叫他不要学“急就章”。这些对尚在保守派唾骂声中讨生活的齐白石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美术史无疑应当补上这重要一笔。
画家王梦白才华横溢,是个有魏晋风度的人,但个性极强又很落魄,作为好友陈半丁对他经常给予接济。1934年画家去世,家庭也陷入窘境。陈半丁借自己在北京画坛的地位和影响,召集北京画坛的众多画家,在琉璃厂集粹山房举行义卖,所得善款全部用来接济王梦白的家小和处理其后事,成为北京艺界的美谈。
陈半丁是二十世纪的篆刻大家,更不失为一个具有文人情怀的爱国之士,他常借印章表达思想感情,并抒发他对现实政治的看法。1937年北平沦陷,他毅然辞掉了国立北平艺专教授之职,刻《强其骨》《不使孽钱》二印为座右铭,坚持以卖画刻印为生,表现出一个艺术家的民族气节。他刻《如此山河》《万牲园中守者》两面印,在边款中曰:“山河如此,民何以堪。半丁闷坐,临危乱之区。”感叹山河被日寇所践踏,将社会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其间又刻《没齿》《中原无人》两面印,在边款中说:“蛇蝎世界,皆由汉奸造成。痛心作此印。”表达对侵略者和汉奸永世不忘的仇恨,同时感叹“中原无人”,对偏安西南的国民党政府所谓 “抗战”进行嘲讽。
1945年,国民党接收大员接收北平,给黎民百姓造成极大痛苦,民怨沸腾。蒋介石派张道藩来宣慰北方民心,并邀请齐白石、溥心畬等画家前往南京举办展览。陈半丁则对国民党政府希望他去南京办展览的邀请,断然予以了拒绝。熟悉20世纪美术史的人都了解,1946年齐白石和溥心畬有宁沪之行的展览,规格之高是空前的,还上演了蒋介石接见、张道藩拜师的戏剧性一幕,轰动一时。所以,接受国民政府的邀请,去南京举办展览,将会给陈半丁带来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他的拒绝在当时令人费解。今天,我们似乎可以从他的一枚印章和边款里找到答案,他于1945年刻《只见江山不见人》一印,抨击国民党政府抗战胜利后的接收政策,并在边款中指出:“胜利尚非实,更何况人乎?一群无耻(之徒),禽兽不如也。”这并不是半丁老人有什么政治上的远见,而是纯粹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本能。所以,陈半丁后来对新中国有感情,绝不是偶然的。
1949年陈半丁留在了北京,他选择拥抱新中国。据陈半丁的档案显示,在1949年,为支持建国事业“与邓宝珊、马占山差不多每晚在马家为解决和平问题,热诚参加活动。至今与傅作义三人信诚如故。”可见半丁老人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也尽了自己一份心力。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代表国家形象的建筑陆续完成,需要布置大量超常尺寸的艺术作品,现代大型建筑的需要,为画家进行巨幅创作提供了历史机遇,陈半丁创作大画的卓越能力得以极大发挥。大凡国宾馆、大会堂、北京饭店、首都机场、政协礼堂、各大博物馆等处,纷纷邀请半丁老人作画。因此,陈半丁留下了大量我们鲜为一见的超大尺寸的鸿篇巨作,也开拓了中国巨幅花鸟画的新面貌,树立了艺术的国家形象。1955年5月,由陈半丁领衔北京14位著名书画家联合创作的巨幅花鸟画《和平颂》,在花鸟画的历史上被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该画的构思则是以陈半丁和王雪涛为主,画面中最为突出的牡丹这一部分,也由陈半丁率先开笔绘制,成为整个画作的画眼,至今为人所称道。
陈半丁的作品还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 1955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老人受命作《达摩像》,并自题五言诗一首:“佛自西方来,乐在东土住。今日送将归,多情勿忘故。”他和齐白石合作的《松石牡丹》,作为国礼赠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前些年回流国内,在艺术市场曾引起轰动,国人得以一窥两位大师的完美合作,据说这是唯一一幅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中国画作品。他为西哈努克在京别墅创作的《四季花卉》,用三张丈二匹宣纸接起来,规模令人叹为观止。
这种既有高度又有宽度的花鸟画巨制,体现了陈半丁驾驭大尺幅作品的过人功力。因此,半丁老人在北京画坛享有崇高声誉的确是实至名归。
解放后,由于艺术市场一度低迷,画家不能卖画,美术学院对众多统派画家也予以拒斥,传统派老画家的生活陷入窘境。陈半丁带领新中国画研究会的同仁展开自救互救,又通过与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的关系,把这个问题“吵”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很快有了“琴棋书画,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去占领。”[ 转自2007年笔者对韦江凡先生的访谈笔录。韦江帆是美术研究所成立之初的办公室秘书]的批示。后经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倡议,开始正式筹建中国绘画研究机构。文化部美术处蔡若虹起草了《国画研究所实施方案》。国家特批十万元专款建所,其中七万元建楼,三万元购买资料。后来又以“中国绘画研究所”的名义,耗资二十万元盖了陈列馆。大楼建成之后,有关部门为了通盘考虑民族艺术遗产的继承和发扬,“中国绘画研究所”遂更名“民族美术研究所”(即今天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美术研究所的建立,其意义决不仅限于解决老画家生计的问题,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的专业美术研究机构得以诞生,新中国美术研究的局面才得以开展,陈半丁在其中功不可没。
在1950年代,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潮一度甚嚣尘上,中国画被认为是不科学的,遭到无情挞伐,国画系在美术学院也被取消了。陈半丁对这种思潮给与了坚决的抵制,并在1956年2月第二次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拟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关案》的提案,他说:“我也算是一个画界关心国事的,从事中国画已六十余年,虽然没有如何成就,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就中国画来贡献一点意见……不幸中国画这一门的进行,较其他艺术如戏曲、音乐,更显迟慢。……并且于中还有一种不顾体念的争扰,就是一些艺专学校,对于中国画一门,似乎就是勉强充数。这样的情况,是无法不就渐衰落的。听说国际艺术家想找人讨论中国画,我们似乎难以答对,更说不到提供专门意见来供国际研究”先指出问题和严重性,继而提出解决方案:“未知政府对于中国画,是否也可以和中医中药一样,设立专门的研究机关,延揽各地专家讨论。并于综合大学、各级师范设立中国画系,分门研究。并多方设法汇集以往优良作品,做深入专门讨论。培养中年、青年画家,予以机会和策励。以扭转轻视国画的成见,打开中国画的出路,发展中国画的前途,走向艺术新建设之路,来配合文化高潮的到来。”[ 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案汇辑》,政协提案第79号]陈半丁的提案,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最终北京中国画院得以在1957年5月14日正式成立,对新中国的国画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半丁居功至伟。之后,广东、上海、江苏等地相继成立了画院,国画创作的局面得到完全打开。
1954年,他为文字改革一事给毛泽东去信。毛泽东回信,希望老人多提意见,对老人关心文字改革深感敬佩,因此陈半丁后来成为“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成员。大约1960年代初,半丁老人曾接待过某日本代表团中的成员,来人不怀好意,声称要和中国人比试书法,老人明白了来人意图,厉声回敬:你们连汉字都没学好,根本没有资格和中国人比试书法。随即连夜就此事上书毛泽东主席反映情况,促成了毛泽东关于“书法要从娃娃抓起”的号召,以及后来在中小学设置书法课程的规定,意义深远。
这就是陈半丁,一个率真而又有着巨大担当的艺术老人。
三.陈派绘画的审美特点
陈半丁的艺术世界,无论是花卉、山水、翎毛、人物,还是书法、篆刻,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且合辙于中华传统文化“雅正”“中和”的正脉,他是深造求通路上的跋涉者和探索者,一方面心仪传统的文人笔墨,一方面又深谙大众的审美审美心理,将文人之雅和市民之俗相融合,赢得了各个阶层的喜好,堪称二十世纪不可多得的诗书画印兼擅的艺术大家。他创作的《共向和平》《春满乾坤》等一批巨幅作品,体现了泱泱大国的雍容气象与新时代的精神意象,也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作品历经近六十年,至今依然在钓鱼台国宾馆、政协礼堂等庙堂之上迎来送往,成为艺术的国家形象。笔者在《中国名画家全集•陈半丁》[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和《斥两极而中行——印之工写及陈半丁小写意印风的形成与特点》[ 载《北京书法家论文选》,北京出版社,2003年]中,对陈半丁的绘画、书法、篆刻的发展脉络与风格有过较详细的梳理和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只略谈其绘画的几个审美特点。
陈半丁是秉持儒家“中道”正统观念的画家,尊重传统,讲规矩、法度、笔墨、气韵。继承了“海派”传统,又有所发展和超越,但与齐白石又有着明显的不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温柔敦厚,中和平正
陈半丁认为:“中国画的境界是诗的境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与画相通于一境。”[ 转引王振德先生2004年绍兴陈半丁纪念馆“陈半丁与二十世纪北京画坛研讨会”上的发言稿]诗以温柔敦厚为正脉。“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以此为诗的灵魂,这自然也是中国画的灵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陈半丁秉持儒家中和的正统观念,在艺术创作上表现为蕴藉含蓄,微宛委曲,深郁笃厚,朴拙平淡,生动自然;既不叫嚣乖张,又不浅显直露,不尚奇弄险,讨巧卖弄。如果拿女人作比,陈半丁是大家闺秀,典雅端庄,落落大方,知书达理,温柔有礼;齐白石是山野村姑,朴素秀丽,羞涩含情,梳野放旷,大胆泼辣。在20世纪这样一个战乱频仍、动荡不安、主义泛滥的时代,在诸多大家之中陈半丁的艺术最充分地体现了温柔敦厚、中和平正的美学。真正能够理解这种柔厚、中和之美,需要有超越时下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和眼光,和静谧的心灵。
富贵气、庙堂气
陈半丁讲求“中”和“贵”,仿佛正人君子,堂堂正正,举止高雅,能见修养、情致、品格之高迈,且有雍容富贵之气,带有一定的阶层意识。如果拿花蔬作比,陈半丁就是总领群芳的牡丹。在中国人眼中,不同的题材表现不同的气象与精神,他不主张不分场合到处都挂萝卜、大白菜,像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就应该画牡丹,庙堂之上就应配上国色天香,四君子虽然文人喜好,但不能取代牡丹的国花地位,这是整个民族的审美决定的。他为钓鱼台国宾馆、全国政协、各大饭店所作的巨幅国画,不事修饰刻画、矜持做作,高雅富贵,可谓是“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意象恢宏,气宇轩昂,平中见奇,摄人心魄,带有庄重大雅的庙堂之气,非大家不能为。
讲求理法
陈半丁画小写意,非常重视传统,同时也讲求理法,即物理、情理、画理和法度。主张“由陈进化”、“从规矩中生变化,由范围内出个性”,其花鸟画造型虽是意象的,但往往叶是怎样长的,枝干是怎么生的,诸如此类,都能合乎生长规律,还善于表现不同环境气候下花卉鸟兽的不同容貌和姿态,意在神似和意境,不事工细小巧,一切自然合理。没骨白描并用,工写兼施,又不失大写意的潇洒风神。
无我之境
王国维将艺术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二者主要是从主体的情感状态表达的显隐来区分的,“有我之境”中主体的情状调动充分,表达比较情绪化,具有丰富的情感色彩和渲染意味,一般呈现为“宏壮”的境界;“无我之境”则主体的情感表达较深曲,心态较平和,一般呈现“优美”的境界。与二十世纪绝大多数画家不同,“陈派”绘画不过多强调自我和个性,仿佛陶诗元画,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乃大我、真我之境,平和冲淡,自然沉静,润物无声。此境看似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实则一切皆因心而造,唯其静,故入人至深,唯其无我,方是大家,这也是真我之境。
总之,陈半丁的人生和艺术,还有太多精彩有待挖掘。一些重要作品一直陈设在国宾馆、政协礼堂、对外友协等庙堂之上,深藏于各大博物馆的画库之中,学术界和广大的观众暂时还无缘亲见,政治上的禁区以及世俗的偏见,学界、出版界、艺术市场现实功利的取舍等等,所以,真正要全面深入了解陈半丁艺术老人,还需要时间,需要更多部门的通力配合,也需要更多学者艰苦付出,不断的考察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