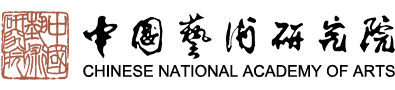王静波
王静波:文学博士,戏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地方戏、戏曲与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著有专著《生肖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邬氏源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论文《富有乡土气息的民间小戏》(《文史知识》2017年第9期)、《荷兰:让非遗在活态中传承》(《半月谈》内部版2017年第1期)等。
笔下有人物 胸中有舞台[①] ——范钧宏戏曲创作研究
该文发表于《中华艺术论丛》第20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版。范钧宏早年接受了良好教育,曾为京剧演员。1949年以后,在不足40年的创作生涯中,独立改编、创作及与他人合作作品4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被国家京剧院搬上舞台,《猎虎记》《杨门女将》《白毛女》等数部成为当代京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宏观的创作观和方法论层面,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开掘历史题材的现实意义;强调完整的艺术构思,注意内容和形式的协调统一。在编剧技巧层面,他兼顾剧本的文学性和舞台性:讲求故事结构的集中,情节的疏密有致;塑造人物的手段多样;创作面向舞台,善于使用和化用程式。总的来说,他擅长传统戏的改编与新编历史剧的创作,也是京剧现代戏创作的先驱。他是一位继承传统、又锐意创新的“推陈出新”的戏曲剧作大家。
关键词:范钧宏 京剧 剧本创作 推陈出新
在中国当代戏曲史上,有一位剧作家,他浸润成长于传统的京剧文化,曾为梨园子弟;他创作了京剧史上多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是中国京剧院演剧风格的奠基人之一,既擅长传统戏改编和新编历史剧的创作,又是京剧现代戏创作的开路先锋;他的理论研究与剧本创作比肩。“理论与实践,台上与案头,剧作与剧论”,[②]兼而擅之者,百年间屈指可数,而他是其中之一。他就是范钧宏。
一 早期经历:做“有文化的京剧演员”
范钧宏,原名范学蠡,1916年3月7日生于北京,祖籍杭州。
范钧宏在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就与京剧结下了缘分。他的父亲是官员,酷爱京剧。在家庭环境影响下,范钧宏从小就是戏迷,不到十岁的时候就成了票友,登台演出的第一出戏是《空城计》,班底是“富连成”。[③]
范钧宏曾立志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京剧演员”。[④]他初中、高中分别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和弘达中学,两所名校的培养使他兼具扎实的国学基础和开阔的西学视野。风起云涌的年代、动荡不安的时局,也影响到了在校求学的学生。弘达中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学生有着参加革命活动的热情,这也影响了范钧宏,其以后的不少剧作中,渗透着深沉的爱国情感。中学时,范钧宏最喜爱古典文学课。初中时,他就为《北京白话报》主编《戏剧周刊》。学生时期,他也曾在京津两地的《晨报》《民言报》《商报》《庸报》《天风报》等报纸发表剧评和研究京剧的文章。[⑤]
年少时,范钧宏一边读书一边学戏。在汇文中学读书时,他曾拜在谭派须生陈秀华门下学唱老生行当。后来,他又先后向鲍吉祥、王荣山、沈富贵等名师学余派剧目,兼学靠把戏和武生戏。[⑥]学生时代,范钧宏曾组建“平平社”,积累了演出经验。18岁时,范钧宏“下海”。他拜在张春彦门下,在梨园公会挂了匾,成为一名京剧演员。
范钧宏正式学戏演戏,是在1934至1940年期间。在前期学习的基础上,由于嗓音条件较为适合,他改学“马派”。虽然没有向马连良拜师,但他大量观摩马派剧目,将唱词宾白及一招一式学习过来,演出时也以马派须生面目出场。据范钧宏自述,在与马连良先生正式谋面之前,马先生曾在一次演出前托人向范钧宏借戏装,可见他早已听闻范钧宏。[⑦]
范钧宏自己组织过戏班。戏班的“承头人”是常少亭(原名常连坤)。“富连成”科班出身的很多演员曾在他的戏班演出,如“盛”字辈的(陈)盛荪、(孙)盛武,“富”字辈的有(茹)富兰、富蕙,“连”字辈的(马)连昆、(苏)连汉,“喜”字辈的有侯喜瑞、王喜秀等。做过程砚秋鼓师的著名艺人白登云也在戏班担任过鼓师。[⑧]
范钧宏演戏喜欢钻研,他琢磨剧本,吃透剧情,力求演活人物。虽然他没有“唱出来”,但是多年的舞台经历,使他熟悉京剧的剧本、音乐、行当、表演流派等各方面。而他的文化修养使他与一般的演员有所区别,多了理性的思考和总结。这就为他日后从事编剧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曾对唱过的一些马派戏进行改动。1937年,他在向高庆奎学戏期间,由于高庆奎只记得自己的台词,范钧宏连记带编,把剧本攒了出来。[⑨]这算是他初步接触剧本创作。
1940年,范钧宏因嗓辍演。之后,他曾任政府文员、剧社辅导、报刊记者等工作。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之前,他穷困潦倒,寄居在亲戚家中。丰富的生活体验,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储备。
二 推陈出新、笔耕不辍的创作生涯
1949年以后,戏曲的地位得以提高,成为人民的“新文艺”。新的时代、新的社会环境,为范钧宏开启戏曲创作生涯提供了机遇。范钧宏自己说“他是党培养起来的戏曲战线的一名战士”。[⑩]1949年,范钧宏加入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11]。同时加入的还有翁偶虹、陶君起、朱木佳、何异旭等。通过学习和实践,范钧宏“渐渐明白了什么是‘新文艺’,什么是‘革命和新文艺的关系’,搞清楚了文学艺术应该为什么人服务,以及怎样去服务等许多问题”[12] 。此时起,范钧宏已经开始了他的创作。1951年,“五五”指示颁布以后,戏改工作正式开始,范钧宏被调至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处。1955年1月,国家京剧院成立,范钧宏被调至京剧院工作。他笔耕不辍,在其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40多部剧本(含与人合作),其中,绝大多数被国家京剧院搬上舞台,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戏曲理论家范溶评价道:范钧宏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推陈出新方面,都给广大戏曲作者以有益的借鉴。”[13]
我们将范钧宏的创作历程分为四个时期:
(一)整理改编和创作摸索期。
加入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以后,范钧宏配合政治任务,写作了一些小剧本,如《三骂媒婆》《王二姐换面》《二流子开荒生产》等。自1953年起,他与一批戏剧家一起,从事京剧传统剧目的整理编辑工作,整理出一百六十个传统剧目,编为《京剧丛刊》,共50集[14]。这些剧本“多数是当时京剧舞台上较为流行的传统剧本,或是在内容和表演艺术方面有价值的剧本,传统作品都以舞台演出本为依据,并吸收有关演员参加整理”。[15]这项工作不仅使范钧宏接触了大量京剧剧本,也使他更好地理解了如何“推陈出新”,学习了编剧技巧,积累了改编经验,使他“完成了从演员到作家的角色转换”[16],也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来源。
1951年,范钧宏接受任务,创作以“信陵君窃符救赵”为题材的历史剧《兵符记》(与黄雨秋合作),代表国家京剧院参加次年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也是范钧宏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创作京剧剧本。作品如期参加演出大会,但是不算成功,原因在于“对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还不甚了解,以至把今人的思想加在古人身上”[17] 。这次创作的经验教训,范钧宏铭记于心,他在以后的创作中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兵符记》后,范钧宏又与何异旭、邱炘、任以双一起,改编评剧《牛郎织女》(1951年)为新编京剧。该剧由郑亦秋导演,叶盛兰、杜近芳主演,作品获得广泛的肯定。
(二)创作黄金期。
1953年至“文革”前夕,可谓范钧宏的创作黄金期。在此期间,范钧宏独立创作、改编,及与他人合作创作或改编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作品有: 《猎虎记》(1953年独立改编)、《陈妙常》(1953年与樊放、杜颖陶合作创作)、《蝴蝶杯》(1954年与范瑞明合作改编)、《除三害》(1955年与吴少岳合作改编)、《岳母刺字》(独立改编,1955年出版)、《三座山》(1956年独立改编)、《陈三五娘》(1956年与人合作改编)、《玉簪记》(1956年独立改编)、《十五贯》(1956年与人合作改编)、《夏完淳》(1957年与吕瑞明合作创作)、《望江亭》(1957年与何异旭、吴少岳合作改编)、《白毛女》(1958年与马少波合作改编)、《林海雪原》(1958年独立改编)、《英雄炮兵》(1958年与张春良合作创作)、《智斩鲁斋郎》(1958年与马少波合作改编)、《捉水鬼》(1958年独立创作)、《柯山红日》(1959年独立改编)、《杨门女将》(1959年与吕瑞明合作改编)、《九江口》(1959年独立改编)、《满江红》(1961年与吕瑞明合作改编)、《洪湖赤卫队》(1960年与袁韵宜合作改编)、《初出茅庐》(1960年与吕瑞明合作改编)、《龙女牧羊》(1961年与许源来、吴少岳、吕瑞明合作改编)、《卧薪尝胆》(1961年与人合作创作)、《强项令》(1962年与吴少岳合作创作)、《春草闯堂》(1963年与邹忆青合作改编)、《战渭南》(1963年独立创作)。[18]其中除《陈妙常》为梆子、评剧通用剧本,《蝴蝶杯》为河北梆子剧本,其余均为京剧剧本。前述多个剧目,成为国家京剧院的保留剧目。
在新编历史剧方面,最能代表范钧宏的创作成就与艺术特色的,有《猎虎记》《强项令》等。1953年,他取材于《水浒传》情节而独立创作的新编历史剧《猎虎记》,被视为他的“起家戏”。该剧在1954年一年内上演一百场,多个地方剧种纷纷移植,于1956年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剧本一等奖。日本也将其移植为歌舞伎剧目。[19]《强项令》是范钧宏新编历史剧创作成熟的标志,经历十年浩劫恢复上演后,成为最负盛名的剧目之一。
传统戏改编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杨门女将》《九江口》《蝴蝶杯》等。《杨门女将》多年来在国内外常演不衰,曾于1960年被拍成彩色舞台艺术影片,获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20]
在京剧现代戏创作的探索方面,范钧宏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现代戏代表作有《白毛女》《林海雪原》等。《白毛女》是1949年以来京剧第一次演现代戏,由阿甲和郑亦秋共同导演,杜近芳、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雪艳琴等著名演员参演,该剧以其独特的创新精神和精湛的表演,获得了巨大成功。[21]
《三座山》是范钧宏用京剧表现真实生活的初次尝试,也是国家京剧院的第一部大型创新之作。它由蒙古歌剧《三座山》改编而来,所以,也有人说作为改变自外国歌剧的现代作品,它的创作实现了“四并举”[22]。
(三)创作衰退期。
1963年,范钧宏积劳成疾,患心肌梗塞,由此创作量下降,只是参与了一些现代戏的创作,如《南方来信》(1964年与王颉竹、吕瑞明、陈延龄、何明敬合作创作)、《山村花正红》(1965年与吕瑞明合作改编)等。文革期间,范钧宏在“牛棚”和干校度过了十年,“一字不出”[23]。
(四)创作恢复期。
文革结束后,范钧宏振奋精神,又创作了系列作品:《蝶恋花》(1977年与戴英录、邹忆青合作创作)、《文姬归汉》(1980年与人合作改编)、《锦车使节》(1982年与吕瑞明合作创作)、《风雨紫金山》(1984年与人合作创作)、《佘太君抗婚》(1984年独立改编)、《玉簪误》(1985年与人合作创作)、《冼夫人》(1985年与人合作创作)、《调寇审潘》(1986年独立改编)。[24]
其中,现代戏《蝶恋花》、新编历史剧《锦车使节》、改编传统戏《调寇审潘》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取材杨开慧事迹的《蝶恋花》在全国引起轰动,在烟台胜利剧场甚至创下连演54场的纪录。[25]《锦车使节》涉及少数民族题材,曾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戏曲创作银奖”。《调寇审潘》是范钧宏的绝笔之作,1987年获“全国新剧目汇演新剧目奖”“优秀编剧奖”。[26]
三 兼顾文学性与舞台性的创作特点
范钧宏不仅是一位剧作大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戏曲理论家。他对于剧目《猎虎记》《蝴蝶杯》《杨门女将》《九江口》《白毛女》《林海雪原》等的创作和改编过程、经验,都撰有文章予以分析、总结。[27]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在动笔创作之前,便有着审慎、理性、周全的思考。他的戏曲理论文章,集中收录在《戏曲编剧技巧浅论》[28]《戏曲编剧论集》中,其论题涉及戏曲结构、戏曲语言、戏曲程式、唱念安排等方面。在研读范钧宏剧作和剧论的基础上,本部分试图对其创作经验与创作特点进行概括。
(一)宏观的创作观与方法论层面
1.他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生活出发,开掘历史题材的现实意义,注重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新编历史剧及改编传统戏,占据了范钧宏作品中的绝大部分。他强调“古为今用”“寓教育于娱乐之中”[29]。由于早期作品《兵符记》出现了“反历史主义”与“概念化”的问题,他充分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在树立主题、构思情节、刻画人物时,注重从历史生活出发,而不带有主观随意性。他在强调主题重要性的时候,将之与“主题先行”区别开来:主题思想“是作者对生活素材观察、分析、提炼之后,有所作为地把生活中蕴涵的积极意义体现于结构之中……这和‘主题先行’又岂能同日而语?……由于作者的生活经验丰富,创作方法对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和真实动人的情节”。[30]
《猎虎记》取材于《水浒》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宝双越狱,孙立孙新大劫牢”,讲解珍、解宝、顾大嫂、乐和、孙立等反抗迫害,被逼上梁山的故事,体现了反封建的主题。剧中每个角色都有其处境和个性特点。比如解珍遇事深思熟虑,解宝则性格暴烈,顾大嫂机智泼辣;解珍、解宝由于毛善与官府勾结,被投入牢狱,顾大嫂等想出劫狱投奔梁山的办法,而身居官位的孙立则有所顾虑,进退两难,在顾大嫂分析利害并采用激将法后,才决定投奔梁山。范钧宏曾说:“张真同志在《剧本》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不要臆造古人的精神面貌》,其中他对于《水浒》第四十九回和对一个戏曲剧本《反登州》的分析,关于怎样描写人物的精神状态在事件发展中(即斗争中)的成长,写出历史发展的‘无法抗拒的逻辑’,以及不能按照作者主观意图臆造古人的精神面貌等原则性问题给我以很大的启发。”[31]而张真看过《猎虎记》之后说:“作者用了现实主义的方法描写人物和事件,就能够大致不差地表现客观现实发展规律,使剧本有较高的真实性,使人能够心服。”[32]
《九江口》和《战渭南》都是写古代战争。传统戏《九江口》写元末动乱时期两个风云人物——朱元璋和陈友谅的一场决定性的军事斗争。范钧宏动手改编之前,在摸了它的三个“底”(历史底、表演底、风格底)之一的历史底之后,肯定该剧“没有从战争双方正义与否的角度,把自己的‘绝对同情’倾注于朱、陈中的任何一方……只是从战争得失的角度,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歌颂了捍卫北汉不计个人得失的张定边、临危应变的华云龙,批判了主观麻痹的陈友谅,“作者没有主观框子,而倾向性又相当明显”[33]。《战渭南》描写三国时期马超与曹操双方的兵家之争。这两个剧目,跳脱了对战争双方的是非评价,而着力于塑造人物,以故事和角色人格力量带给当代观众启示。
《杨门女将》与《满江红》与上述二者不同,它们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体现了作者对于历史和道德的评价。但作者对杨、岳两家的“忠”也是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以岳飞抗金被害的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很多,“有的剧本在歌颂岳飞的报国壮志时,尽量渲染了他的愚忠思想”[34],而范钧宏对“忠”的二重性做了正确判别,“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永远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