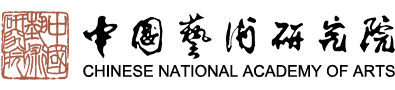王学锋
王学锋,文学博士,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戏曲与地方社会、戏曲文献研究。著有《民间信仰的社会互动——山西贾村赛社及其戏剧活动》(台湾学生书局,2012版)、《南贾赛社》(上、下)(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版)等。发表《清宫演剧用本〈太平王会〉初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第4期)、《《大武若文:戏曲武戏摭谈》》(《文艺报》,2017年5月22日)等数十篇。参与《京剧艺术大典》《中国大百科全书 戏曲卷》(第三版)等课题。
基层本位•史诗趋向•创伤书写: 评剧《母亲》的三个维度
该文发表于《戏友》2018年第5期。评剧《母亲》既是对过去冀省基层乡村的个人和家庭的抗战史的一次重新书写,也是对发生在抗战年代基层社会的无数个体和家庭的悲怆遭遇的深情再现和艺术抚慰。其民族和革命叙事都是连带、紧贴着基层叙事进行的,是有别于(革命)精英叙事的民间/基层叙事,既是基层乡民的抗战故事,也是八路军的基层战士的抗战故事。虽是基层故事、基层叙事、基层本位,表达上却有史诗般的趋向和品格,强调乡土中蕴含的生命诗学乃至文化哲学。而在对主人公母亲这一平凡女性的人生史书写时的创痛展演中,既揭示了身份认同的艰难转换,又反思了线性的胜利史观,最终召唤并抚慰了那些现代“进步”观念所遮蔽的灵性个体。
近日有幸观看了锦云先生编剧、张曼君女士导演、王平女士主演、中国评剧院合力精心制作的评剧《母亲》,觉得是当代戏曲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值得认真释读、认真学习。
这是一部描写基层民众抗战历史的戏曲作品。戏曲中的抗战书写不少,关注基层民众的也很常见,但以基层的乡民为书写主体、主人公的却较为少见。本剧故事发生在原属河北的京郊密云县张家坟村及周边一带,主人公邓玉芬是村中一位普通而平凡的女性,日本人把她和家人赶出了家园,关进了“人圈”,她和家人几乎无法活下去,于是她的几个儿子投了八路,她和老汉逃到附近的猪头岭支持八路军抗战,但在抗战中她悲痛地失去了家中所有的亲人。本剧取材自真实生活,既是对过去冀省基层乡村的个人和家庭的抗战史的一次重新书写,也是对发生在抗战年代基层社会的无数个体和家庭的悲怆遭遇的深情再现和艺术抚慰。
本剧是以母亲邓玉芬对抗战经历的回顾为主要视角的,并伴以母亲和小仔儿(第五个儿子)等人的对话,众乡亲作为背景也充当了“民众”这一叙事人的作用,因此,本剧是以基层乡民的叙事为主调的。此外,本剧兼顾、容纳了民族叙事(文化叙事)和革命叙事(八路军叙事)。但重要的是,民族和革命叙事都是连带、紧贴着基层叙事进行的,并且是以基层乡民的叙事为本位的。如第二场,随着“民国二十六年,华北起狼烟”,乡亲们被日本侵略军赶入“人圈”,大家悲愤地唱出:“中国的年不让过,中国的节不让过,中国的字不让写,中国的话不让说。”母亲也有力唱出:“在我的家,我的国,我的炕头,我的饭桌,吃我的粥饭,还要感谢一个欺我抢我杀我害我的大恶魔!”外敌入侵,生存环境被挤压到了极为严酷的地步,家、国皆临危难,传统乡村中的民众迅速建立了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民族叙事也随之瞬间确立。但这一群体性的民族认同,又是从切身的文化经验和乡村经验出发的:我们中国的年、节、字、话,我们乡村的炕头、饭桌、粥饭。这样,从乡村到民族的话语转换,毫无违和之感,即便民族叙事有时高高扬起,但仍要落在基层叙事的话语大地上。
对革命叙事的处理也类似。剧中既没有出现革命的敌人如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军等人物形象,也没有出现革命的精英、领路人如惯见的英雄、党代表、部队干部这样的人物形象,他们都是在背景中出现的。日本侵略军没有出现不必多说,八路军干部也是作为背景在众乡亲的口中出现的:“云蒙山上红旗展,来了八路第十团。团长就是白乙化,军民抗日保江山。”对八路军的描写也是带着鲜明的乡民经验和视角的,如八路军战士小郭出现时被形容为“危难中的神仙”,如猪头岭小石屋过年时老汉所唱:“先拜关老爷,大刀劈杀日本鬼,再拜姜子牙,神机妙算定中原。哦哦,更拜咱八路神将小白龙,呼啦啦抗日大旗红半天。”八路军是神,日本兵是鬼,神鬼之别,乡亲们分得很清楚。真正出现的八路军人物形象都是八路军的普通战士,母亲的四个儿子是八路军的普通战士,帮助母亲逃出“人圈”的小郭也只是八路军的一位普通战士。值得注意的是,本剧第四场描绘了猪头岭山坡前,已成为八路军家属的乡亲们纺织的一幕。这些都提示我们,这是一部不一样的革命抗战故事,是有别于(革命)精英叙事的民间/基层叙事,既是基层乡民的抗战故事,也是八路军的基层战士的抗战故事。在本剧中,八路军子弟就是普通老百姓家中的子弟,基层民众就是八路军的深根,两者深刻相连。可见,本剧的革命叙事也是紧密关连着基层叙事的,就像对民族叙事的处理一样,也是以基层叙事为本位的。这一基层本位的叙事法,可谓对以往单一的、固化的民族抗战史、革命史的有效补充。
虽是基层故事、基层叙事、基层本位,但本剧在表达上却有史诗般的趋向和品格。一方面,这个抗战故事展示了民族叙事的维度,必有其宏大的关怀。另一方面,剧中可见创作者对民众中蕴藏的生命力和生存力的推崇,试图展示其生命诗学。如对母亲大脚的处理。第一场母亲对自己大脚陈述:“六岁上亲娘给俺裹小脚,姑娘脾气拧,把裹脚条子给扯下。两只脚片由性儿长,白白生生肥又大。”强调的是本性和本能,是生命的原生力,不受束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没有将放脚的观念指向“五四”式的现代观念,而是导向对生命本能的抒发。第二场对大脚又有回应。小仔儿问娘:“您,逃得了吗?”小仔儿此问既是作为儿子的担心,也是众乡亲/观众的关切和疑问:您一个农村老太太,能跑哪儿去?母亲的回答很给力:“多亏你姥姥,给妈这双——大脚!”有大脚就可以逃,逃就有活下去的机会!本剧在此处高扬了乡众的生命本能和传统乡村一代代传下来的生存伟力。剧中的传统乡村既非落后、愚昧之地,也非田园风情、浪漫乐土,当然也不是对民间文化、民间趣味的单纯展示,而是在书写时强调其乡土性,乡土中蕴含的生命诗学乃至文化哲学。宏大关怀和生命诗学在艺术上得到了有力的、史诗般的支撑和呈现。如中西混合乐队展示的情感表现广谱,既气势恢弘、厚重凝练,也悲怆痛切、如泣如诉,也温暖祥和、静谧无声;如借助合唱、群舞等群体语汇着力进行的展示、烘托、渲染。而对对戏曲假定性运用的熟稔融通,对以母亲为主叙事人而辅以小仔儿、众乡亲的多重叙事人的综合采纳和灵活变换,对事件和情节的凝练表达和高度概括,使抗战八年囊括其中、和盘托出,也呈现出史诗般的气魄与视界。
以基层乡民为本位,弘扬其生命史诗,无疑具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而在对主人公母亲这一平凡女性的人生史书写中的创痛的展示中,却有主创者的体贴和洞见,这一点是更加感动人的。
伴随史诗般的展示的,确是首尾一贯的创伤书写和抚慰,并在第五、六场的认子和杀子中渐达高潮。开场,芸芸众女性中浮现出了主人公母亲,“望儿归”声里,母亲沉浸在回忆之中,她既想跟众乡亲说说话,更有难以道与外人的絮语。孤寂的母亲无以排遣对亲人的思念,唯在记忆的碎片中团聚家人。小仔儿和老汉及4个儿子接连显身,引动了创伤的呈现和抚慰之旅。小仔儿既是第5个儿子的魂灵,也是失魂母亲的心灵对话伙伴,他既变幻为情境中的某些人物,也是观众的舞台外化。有了思念最深、最痛心魂的小仔儿作伴,也许母亲的这趟回忆/记忆之旅可稍作安息。这是典型的创伤症候:创伤几乎是难以愈合的,唯在重复中获得舒缓。接下来的场次,小仔儿如影随形,伴随着母亲诉说着过去的一幕幕。第五场猪头岭山坡认子,是个重要的转折。母亲在前场看过了邻居家的孩子喜鹊生生离别了自己的妈妈,此处要自己来决定儿子的生与死了。母亲唱道:“这一个十月怀胎亲生下,那一个亲娘千里望儿正倚门。这一个土生土长蒙山下,那一个为抗日离别亲娘到密云。”“抗日”连接起了每一位“望儿归”的母亲,小郭和自己的大儿子永全都是八路军的子弟,也别无特定的认领小郭或永全的理由(没有谁手握情报之类的“特权”),选别人的孩子而不选自己的孩子,唯一的理由就是“无私”,是抛弃血缘纽带,彰显共同命运和群体利益。这是残酷战争中最理性的选择,群体彰显,个人退隐,没有群哪有私。但这对任何一个母亲来说,显然都是永久的创伤性选择。永全被杀,小郭冲过去抱住母亲喊妈妈,母亲“嘶声悲嚎”的却是:“我的永全哪……”此刻,她返回到了“私”。第六场杀子,母亲几乎没有机会再返回到她的“私”。母亲和众乡亲及八路军伤员躲在山洞,小仔儿啼哭不已,为避免暴露使整个群体都丧命,母亲亲手捂死了出生不久的小仔儿。从认子到杀子,母亲经历了“母亲”身份认同的转换与再造。认子,认别人之子为自己的儿子,是“母亲”身份的认同转换,杀子,就是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身份。“母亲”形象的再造,却是以“母亲”身份的阉割为代价,对一个女性的个体来说,这是不尽的创伤。
抗战胜利,不同于线性的、进步的胜利史观的呈现,即便外敌已消失,母亲仍没有从丧子的创痛中苏醒,戏剧在此有一个延宕,真实的延宕。母亲唱道:“云蒙山家难国难相逼紧,眼睁睁送走老汉儿子六个亲人。”只有从“家难”升华为“国难”,只有两者相连,伤痛才得以舒缓,只有抒发伟大的情怀“人团圆享太平”,母亲才可在创伤中获得疗救和抚慰。
抑或,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抚慰。当20世纪以来的现代观念祛除了“鬼魅”之后,游魂就一直飘荡在历史书写的各个角落。剧终时,“红衣喜鹊横穿舞台,一声声呼唤:妈妈,妈妈……”还有哪些逝去的英灵,魂兮归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