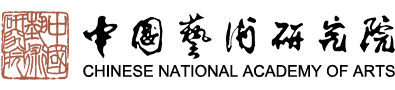王 馗
王馗,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戏剧戏曲学系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戏曲研究》主编。本人主要研究领域为戏曲史、戏曲理论,兼及宗教民俗领域,较为全面地涉猎了关于戏曲历史和现实研究的多元领域,并在相关的专题研究中拥有前沿成果。本人秉持田野调查与历史考证、古典文献与艺术评论、戏曲艺术与民间社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本人努力在学术研究中打通古典与现代、案头与场上、艺术与社会的基本思路。著作有《偶戏》、《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鬼节超度与劝善目连台北》、《孤山的文人影像——三百年小青热辑事论稿》、《粤剧》(中、英文版)《梅州客家佛教香花音乐研究》、《解行集:戏曲民俗论文集》、《京剧史料汇编(清代续编)•行会文献》等。
戏曲之道 ——谈中国戏曲艺术的体系与理想 ——谈中国戏曲艺术的体系与理想
该文原刊于《人民政协报》2017年12月11日第11版,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舞台艺术》2018年第2期上全文转载,同时被《新华文摘》2018年第5期全文转载。全文从文与艺两个角度,呈现了“戏曲”在体系建构时呈现的两种学术视角和具体实践,指出在乐文化的要求规范、在礼乐观念的指引中,文人视角与艺人视角中的戏曲艺术体在社会功能和文化传统上趋于一致。按照戏曲活态传承发展的规律,中国戏曲在体系结构中呈现出相互影响、多元并生的类别特征,形成丰富的体系结构,并呈现出共通的表演美学理想,特别是从中国戏曲古典时期以汤显祖为代表的理论建设,阐述了戏曲在塑造形象时最高的艺术境界要求,以及艺术创造过程与手段表现。
原刊编者按:戏曲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独特的戏剧文化,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又散发着年轻的活力。中国戏曲在经历漫长的孕育、衍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体系。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戏曲有着独特的魅力。本期讲坛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研究员从戏曲艺术的“文”与“艺”入手,对戏曲艺术的形态及其中国戏曲精神进行解读,他以其严密的逻辑思维、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含蓄不失通俗地解答了中国戏曲的传承和发展的问题。此次讲座是王馗研究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生院戏剧戏曲学系共同主办的“前海讲坛”系列讲座的首讲。现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戏曲艺术的“文”与“艺”
“文”与“艺”是戏曲从诞生以来就被确立的两个重要视角和艺术范畴,由此呈现出很不相同的戏曲面貌,展现出对戏曲很不相同的解读途径和方法。
明代曲谱《太和正音谱》在引述赵孟頫的话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在良贱有别的传统社会里,社会不同阶层适用和评价戏曲的方式自然有所区别。
戏曲成熟之际就受到文化人的重视,这不但表现在那些屈居下僚的文人投身于戏曲文本创作,由此不断地提升着戏曲在表情达意的厚度和深度。当然,到了明代以来,众多文人精英将视野转向戏曲,带来了古典戏曲文学的高峰创作,而且表现在戏曲的社会功能被高度肯定,即如胡祗遹在秉持“乐与政通”的传统观念时所强调的“伎技亦随时所尚而变”,因此,在元杂剧出现的“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得其态”(《赠宋氏序》),就数百年来中国戏曲就成为重要的载道工具,戏曲艺术的发展就必然与社会主流价值相一致,在抒情写意中走向高台教化。而戏曲艺术体的重要承载者———底边社会的乐人群体,则秉持着剧场戏乐的娱乐精神,在包括傀儡戏在内的戏曲艺术中强化着“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梦粱录》)的褒贬寄寓,用传承和创造的各项技艺,如滑稽、诙谐、戏弄、歌唱等多元化的技法,回应并拓展着文人的艺术理想。他们的舞台创造既局限于时代,也通过累代相积而超越着时代,在不断地发展中实践着与文人同样的文化诉求。殊途同归的基础,即在于戏曲艺术的肇端即为源远流长的礼乐观念和礼乐实践。
作为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戏曲高度整合了传统礼乐文化的几个重要艺术形式:诗、乐、歌、舞,将先秦以来就形成的乐舞一体、诗乐一体、诗歌一体等具体实践进一步整合,综合成庞大而独具特色的表演艺术体系。乐是器乐体系,统领戏曲的节奏与结构,构成对乐文化的直接反映与接纳;诗是文学体系,是戏剧性的基础,接续的是“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传统;歌是声乐体系,是戏曲情感色彩的载体,也是戏曲流化社会各人群的重要方式;舞是表演体系,是用行动来配合文学演唱、用韵律来彰显音乐节奏的再现手段。四者相得益彰而高度融合,并且与时俱进,直接契合着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与恒久传承的礼乐观念。因此,在乐文化的要求规范、在礼乐观念的指引中,文人视角与艺人视角中的戏曲艺术体在社会功能和文化传统上是一致的。这也决定了两个层面的戏曲,虽然会有很多实践中的抵牾,例如文人对于戏曲民间性的贬责、禁止,艺人对于戏曲的文人化倾向的改造、俗化等等,但是就戏曲本体而言,是丝毫无损而形成更加多元的艺术发展规律。
戏曲艺术的“文”与“艺”在近代以来的理论研究中依然存在。所谓的“文”,即文献、文本、文学,这三者共同推进了传统戏曲的研究,孕育出近百年戏曲史论的丰硕成果。从文献学的学科规律来契入戏曲研究,是传统学术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方法,是戏曲学在传统学术体系中得以孕育成熟的基础,以文献的辨识与考实为基础,奠定戏曲史的基本面貌,这是戏曲研究工作的必由之路。通过广泛的文本研究来拓展戏曲研究的局面,在传统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文字、图像、文物等多元的记录文本纳入研究范畴,全面呈现,深入深掘,带来戏曲研究领域的全面铺陈,这是戏曲研究工作的拓展之道。从文学高度来引领戏曲研究,不仅仅在于以“诗”为代表的文学是戏曲艺术的灵魂性指标,还在于它内在地规定了戏曲艺术的文化特征与制度属性。由此也造就了戏曲史论之外的戏曲批评,始终处于从外部考察和引领戏曲发展的状貌,显示着戏曲研究更加丰富的阐释空间,增加了戏曲解读的深度和高度。
所谓的“艺”,主要包括舞台、表演、实践,这三者张扬的是戏曲作为艺术而呈现出来的“行内之学”。作为一个与戏曲发展相伴始终的领域,舞台艺术呈现的是戏曲活态的存在规律,在空旷而变化的一方舞台上,从四面观到三面观、镜框式舞台,直到今天的小剧场探索,都是在观演关系中实现了戏曲艺术的成长,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戏曲的时代性变化。表演艺术呈现的是戏曲借助身体韵律与技巧呈现出的表达规范,体现的是人的创造性,以及创造力对于戏曲养成的作用,由内心感发而至形体表演,由演员而成就形象,这是戏曲创造舞台境界的重要途径,也是“表演”得以成立的前提。实践艺术呈现的是戏曲与社会人生所构成的生态联系,这个生态既是舞台艺术自身的,即依靠多元结构的表演团队而创造舞台面貌;同时也是舞台内外互动形成的,即依靠观演而让戏曲驻足于特定社区和群体生活中。这使得戏曲研究的视野必须及于当前的创作作品、当代的艺术规律、当下的观演者,并且让戏曲之学上升到政策之学,用浓郁的学术总结和规律把握,来实现戏曲的跨时代延续和发展。
戏曲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实如陈独秀提倡的“戏园者,实普天下人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在延续着精英化的文本、文献、文学研究的基础上,以舞台为基础的艺术之学、以本体为旨归的表演之学、以社会功用为基础的实践之学逐渐地凸显出来。这也是戏曲理论研究可供长效拓展的重要领域。因此,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成为60多年来戏曲研究的重点,这不但极大地拓展了戏曲研究的方法领域,而且也接续着千百年来的戏曲发展规律与艺术传统,这也是今天必须张扬前海学术的重要原因。
戏曲艺术的形态
在戏曲研究工作中,必须广泛吸收借鉴“文”、“艺”视野中的戏曲研究成果,综合使用多元方法,强化中国戏曲艺术规律和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建设。
前海前辈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有被称作“前海学派”)身上体现出的富于开放性、包容性、现实性的学风,启发着今天的后学者用扎实稳健的学术成就持续推进中国戏曲的现代进程,辅助戏曲政策,不断完善戏曲生态的良性建设。当然,必须看到当代众多学术视野与领域的拓展,对于更加丰富前海学术的必要性。例如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介入,使得戏曲理论与实践得以交融进一步成为可能。包括近年来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这都不断地提示着戏曲界:只有理论与实践的更加贴近,才能更加契合中国戏曲的文化本原和艺术理想。
中国戏曲艺术体系内蕴涵的偶戏、宗教祭祀戏、古典戏曲、近代戏曲、当代戏曲、少数民族戏曲诸形态,以及每个形态的现代拓展,由此形成了各具规律、相对独立、交相互渗的民族戏曲体系,这是以前海学术传统为基础的戏曲研究进行民族化理论建构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戏曲千百年来的发展历史和地域创造,“剧种个性”是戏曲艺术在技艺手段之外的艺术经验,戏曲的传承发展需要维护和拓展特定剧种的艺术规范,这也是维持戏曲精神风骨的重要方面。中国将近350个剧种,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每个剧种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地域审美以及不同时代的人的创造,就造就了自具个性的艺术品格。木偶皮影形态、宗教祭祀戏剧形态、古典戏曲形态、近代戏曲形态、当代戏曲形态、少数民族戏剧形态,相续发展,彼此交织,凝练成各有趋向的艺术体系。
偶戏也称傀儡戏,以木偶戏、皮影戏为主,是凭借偶像这种特定的物质载体来创造的表演体系。木偶戏主要是借助于人操作偶像的方式进行表演,而皮影则是侧面影身与光影效果进行表演,偶戏是中国戏曲艺术中最早成熟的表演艺术,去偶化也造就了很多的当代剧种。偶戏的千年传统提供了理解戏曲的独特视角,即如何在质朴的品质里看到中国人游走于天人之际来探寻戏曲本质?唐代林滋撰写的《木人赋》高度评价的偶戏艺术,正解答了在浑朴天然里探索人类之外世界的艺术理性,这是至今需要引起关注的。
古典戏曲形态是封建社会中后期戏曲从属官方乐籍管理体制而形成,极力奉行诗、乐、歌、舞一体的表演理想,尤其是莆仙戏的“傀儡介”、梨园戏的“一句曲一步科”、昆曲的“有声皆歌、无动不舞”等原则,极大地彰显了这一形态的艺术规律。由于官方文人的参与,古典戏曲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乐论、文论、剧论)颇为完善。古典戏曲的这种特质决定了中国戏曲至今仍以古典遗存的经验与理论作为基础,戏曲讲究以昆曲为师,昆曲是百戏之师,正是古典戏曲庞大的艺术与理论成就荟萃于昆曲的事实使然。特别是古典戏曲的时代中,目连戏和傩戏是极具宗教特征的独特形态。中国戏曲一直是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傩戏是礼文化中分衍出的形态,傩礼近乎戏,十世纪以后逐渐地戏剧化,至今仍然以“亦戏亦仪”的演剧特点,发挥着社会礼仪化的作用。而目连戏则是以剧目形态,兼容了丰富的表演艺术,而形成独特的演剧现象,深入地与节日庆典和信仰礼俗相融合,并且与各地地方经验相一致,成为展示思想道德伦理教化和寻求精神追求的重要艺术体。
近代戏曲是从清代雍正元年废除乐户以后,中国戏曲得到了自由创造,由此呈现出师法古典而多有超越的一类庞大体系。例如它遵守的虽然是诗、乐、歌、舞为一体的表现形式,但是它的诗多趋向于民间风格的诗,尤其是用突破曲牌体限制的长行诗歌,写景状物、表情达意更加自由灵活;它的乐也变得更加自由,不受格律限制的板腔体、小曲体等多元形式,而能深入到中国各地民间音乐的艺术海洋中,随处取用,酣畅地表达基层审美趣味;它的舞也可以单独呈现,甚至走向炫技,在传统曲意诗文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对身体和舞台道具的表现力充分结合起来,彰显出丰富的舞台动作性;它的歌也因人而有更多创造,不但沿袭传统以来多元丰富的声乐艺术,而且因时、因地、因人、因审美趋向,创造出属于时尚流行的音乐演唱。在这些剧种中,以舞台官话为主体的京剧,和以方言为主体的粤剧,都是综合南北戏曲艺术精华后形成的大型剧种,一个号称国粹,成为近代戏曲艺术的最高典范;一个海外流播最广,是地方戏艺术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两个重要的代表性剧种极大地展示着近代以来中国戏曲的创造经验。
当代戏曲样式则是随着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而出现的艺术形态,包括20世纪以来特别是50年代新生的剧种,以及不断被创造成熟的现代戏,其创作手法在多元的审美娱乐中更加丰富。特别是现代戏一改传统穿戴和传统生活的限制,将戏曲与生活的联系予以充分强调,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属于现代表现手段下的表演体系,这是对于以古典为基础的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重大拓展。
在少数民族戏剧形态中除了藏戏、傣剧、壮剧等古老的民族戏剧样式外,很多少数民族剧种以浓郁的当代创作方式,不断地拓展并形成各自的剧种个性,例如蒙古剧包括了以长调、短调作为其音乐本体的形态,也拓展出了向歌剧、音乐剧学习的艺术规范。无一例外,这些少数民族戏剧形态大多从本民族的歌舞艺术中戏曲艺术元素,形成以歌舞为基础的戏剧化表演,既是多元一统的中华民族崇尚礼乐文化的形式延续,也是发展民族表演文化的重要创造。现当代戏曲形态与众多少数民族戏剧形态的艺术体系是开放性的,艺术创造的空间还很大。戏曲理论与实践者都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宽容,去理解和接纳它的创造,甚至是完全颠覆传统意义的戏曲创造。
戏曲艺术的“道”
中国戏曲精神是发展创造的精神,不是僵化的固守传统。传承不是模仿,而是在时代相传的前提下不断地再创造,并始终与社区群体保持认同感,维护其持续性,如此才能体现出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属性。即以昆曲为例,昆曲在近代以后走向衰落,昆曲艺人固守着悠久的艺术传统,这实际上只是表象,因为昆曲精彩的折子戏已经被历代艺人推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高度,昆曲能够以折子戏作为艺人安身立命的资本,即在于那些累代相积的创造之功,和新一代的昆曲传承者不断接近传统而为昆曲经典剧目带来的常演常新的艺术魅力。而今天,一代代的传承者们实际也以符合时代的创造性,来不断地延展着经典的境界。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的变化是永恒的,艺术的创造当然也是一样。戏曲不需要追求固定不变的舞台印象,而应该始终尊重人的创造。
中国戏曲的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要以中华民族戏曲艺术的本位立场,高度重视千百年的中国戏曲发展史所形成的丰富理论资源。如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标榜的戏曲之“道”,即总结出了中国戏曲艺术得以养成的纲领性理论,以及上下千年的艺术实践理论,这正是建构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理论源泉。
早在400多年前,当中国戏曲艺人处于最底层时,汤显祖看到了他们承载的艺术是如此伟大,也清楚地了解伟大的戏曲艺术是怎样一点一滴地被塑造出来的。因此,汤显祖站在传统文化的流程中,给中国文化进行了最具高度的戏曲艺术理论总结,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他把中国戏曲的行业祖师,放到了与佛家释迦牟尼、儒家孔子相提并论的高度。他所标识的戏曲艺术理想集中地体现在这篇文献中对于“微妙之极”的戏曲之“道”的阐释。用今天的概括,即戏曲演员通过严格的身心训练,让戏曲舞台生发出无限的艺术面貌,其艺术创造阶段有四个方面:第一,摹形求真;第二,融技演艺;第三,化心为境;第四;取意进道。
摹形以求真,即通过严格的传承和修炼,在看似“照猫画虎”的方式下,掌握传统,展现舞台艺术面貌,这恐怕是所有表演艺术共有的阶段。戏曲通过对艺术形象、舞台场境的摹写,让真实的生活体验获得舞台质感,最终如《乐府传声》所表达的“设身处地、形容逼真”,演绎社会各阶层人物及其生活,以此达成与观众的真实沟通与体贴。
融技演艺,即通过唱、念、做、打、舞、表等诸技艺手段,特别是适用多元程式,来呈现舞台艺术美感。传统戏曲中的同样一套功法技巧、音乐舞蹈,在不同的剧目中、在不同的角色关系间、在不同的人物情景中,都会焕发不一样的艺术风采,这就让戏曲从诸多的表演艺术中,逐渐地摆脱了格范的刻板束缚,而成为可以依靠演员进行灵活塑造的艺术。近代以来中国戏曲的分化演变正是基于“艺术”的理由,而不是单纯的技巧技法的逻辑。用技法训练作为手段,追求艺术化的舞台创造,是戏曲作为艺术的重要基础。
化心为境,即通过演员将个体内心世界与形象场面予以融通变现,如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所提到的“郭石洲言”,男性艺人借助化妆等方式可以呈现一个舞台上漂亮的女性形象,但终归是要“化心为女”,“吾曹以其身为女,必化其心为女,而后柔情媚态,见者意消,如男心一线犹存,则必有一线不似女”,戏曲舞台上的人物形象最终是典型化的,这正是戏曲舞台境界之所在。这也就意味着不论是男旦、坤生,其真正传承的是属于中国戏曲的艺术境界,而不是简单的“女形”、“男形”。特别是引领戏曲的重要元素“诗”,所要求的是心灵的艺术,戏曲艺术最终归结到人心的创造、人心的变化,以及人心无限的丰富和拓展。因此,戏曲应该永远求新、求变、求发展,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外化,这也意味着它本该是年轻的艺术,创造者要思考在不断变化的时代审美中,如何去孕育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这也是“化心为境”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取意进道,即戏曲艺术的终极追求是与哲学、文学所追逐的至高理性异曲同工,特别是“意”是中国传统文艺中的重要范畴,是微妙的、不可言说的,“意”的存在引领着戏曲的一代代艺人在终身传承戏曲过程中,用身体来驾驭舞台规律,用生命来体会舞台艺术,用心灵来张扬舞台魅力,由此实现在声音与表演中,诉诸精神沟通的“微妙之极”的艺术之“道”。这正是几百年前在戏曲行业中就树立起来的至高标准。
今天,当学术研究还在充分利用和沿袭上世纪80年代前海学人所奠定的理论基础时,不论是前海的后继者,还是戏曲领域的其他参与者,都应该充分地理解并尊重戏曲艺术在千百年来形成的艺术体系,都应该强化并奉行戏曲艺术在古典时代就已经被总结出来的艺术理想。那个被称为“道”的戏曲艺术,既是哲学层面的文化体,同时也是实践层面的艺术体,哲学与艺术高度统一,这是中国戏曲不局限于表演艺术的特点所在,也是传续中国戏曲时,必须要将它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与文化理想建立联系的关键所在,当然也是中国戏曲在世界艺术中得以成为彰显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