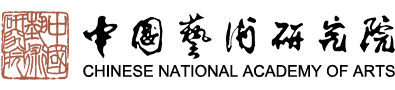陈文璟
艺术管理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书画评论家、著名策展人。
好画知时节——传世名画里的春夏秋冬
本书以文化传承视角切入,解析中国传世名画,用一叶知秋的方式让读者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欣赏更为整体和宏观。春夏秋冬,寒暑相继,本书由古代中国画中自然界的变化引申至文化认知,体悟历代名画的文化意义。该书结构分为四章:第一章,春:“夜静空山”与“万紫千红”;第二章:夏:“蝉鸣声声”与“夏荷涟漪”;第三章:秋:“慎终追远”与“东篱赏菊”;第四章:冬:“雪梅冷逸”与“寒林萧索”。每章分别抓住季节中两个核心主题,选取对应的经典画作,对其进行研究解读,深入分析,呈现了作者对微观画作到宏观文化的思考。本书重点读画,又不止于读画,也读画家,读历史,触类旁通,追根溯源,通过文化传承看中国绘画艺术,通过中国绘画艺术看文化传承,对传世名画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绘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它依然是能够体现民族价值观的体系性存在。
本书由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第一章 “夜静空山”与“万紫千红”
对于春天,中国古代画家有着各自的理解,大概可以分为“夜静空山”式的空灵隐逸和“万紫千红”般的世俗休闲。两者各有千秋,相映生辉,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绘画经典中的“神话”。前者以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为意,意在笔先,试图将画者心中之春意渲染于纸面;后者当以朱熹的“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为纲,纲举目张,重在描写人与自然的融洽和谐。进一步而言之,两种绘画类别虽然体现了中国文化有史以来的两种思维模式,但其审美趋向却可以归之于一点,即郭熙所谓的“春山淡冶而如笑”。所谓“笑”者,不唯画者自笑于笔墨之间,抑或笑人们留恋于春天而惘然不知四季之更替,不舍昼夜。苏东坡曰:“……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我国最早的山水画之一有展子虔的《游春图》,绢本,青绿设色,画上有宋徽宗题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宋代之前,中国绘画大多没有名字,更无落款和作者签名,所以皆由后人因绘画内容而题写画名,或许未必是画者本意,却依旧可以假设如是,此图即如此。纵观此图,青山叠翠,桃杏芳菲,确实写的是春天气象,笔墨技法虽然尚显稚嫩,但春意盎然,溢卷而出。
后期的唐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与此图不同,以鲜衣怒马的人物描写,以杜甫《丽人行》诗意为文化背景,使人们既可从画中人物的从容懒散中体会到春天的适意,又可从其成熟的人物勾勒中体会艺术美。所以,相对于《游春图》的稚拙,这幅作品更适合作为中国画“游春”题材的开始。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杜甫以写实的文笔抒发字外之旨,张萱以写实的画风抒发画外之音,在展现现实意义的层面固然有深有浅,但于艺术审美来说,或许“美”是一个更加直接客观的“审评”标准。在这里,绘画主题人物不再是“成教化、助人伦”的忠臣孝子,主题故事更不是经典故事的解读,而是将绘画理想的落实转向了现实生活,绘画视野不再局限于文学作品的补充,而在于自我表达的审美诉求。可以说,自唐朝中期,长期的社会安定,导致社会经济的极大繁荣,科举制度的推行又渐渐消除了门阀势力,平民百姓在文化发展中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使中国绘画于此时才一变而成为独立的文艺门类,中国绘画的春天真正开始。实际上,《虢国夫人游春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神话”样式的世俗化开始。毕竟读过《世说新语》的人都会不免将魏晋人物当作一种风骨存在。彼时顾恺之写的《洛神赋图》是何等缥缈恍惚,衣袖如云,飘飘若仙。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性的显现,让我们开始重视自性,跨越门阀豪门界限,真正落实“有教无类”的文化理想。以此观之,彼时的魏晋人物原来也不过如此。比如阮籍号称不臧否人物,却将那些出入朝野的人物比作裤裆中的虱子,以为其所追求的富贵名利并不足以保身。那阮籍自己呢?还不是靠着司马昭的庇护才勉强过关。一旦失去这层保护,他对人生没有任何把握。所以,别人的春天不是真正的春天,属于自己的春天才是最真实的存在。《虢国夫人游春图》展示的是一种姿态,是画家开始关注现实社会、关注自身情怀的开始。
不过,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其实不是唐代摹本,而是宋代摹本。从收藏角度来说,绢的寿命最多也就1000年左右,则即使原作未曾遗失,在今天也可能化为乌有。何况,宋代摹本并非今人的粗制滥造,更非通过炒作等诸多方式进行层层造假,而是一种绘画技艺的图像留存,具有很高的艺术文化价值。双线勾勒的笔法更加忠实于原作,在人物造型和神态描写上都能做到圆润秀劲,将人物的雍容自信和休闲懒散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甚至,恰恰因为画家的主动学习和实践,使古代绘画的摹写有别于机械地复制,在尽量保持样式的前提下,更多绘画之外的文化传承能够鲜活地保存下来。谢赫六法中专门有“传移模写”之说,即是表明其所摹写的文化内容不应当局限于形式表面。一如冬去春来,年年花开花落,看似相同,其实万事万物却没有停止过变化,至少拍照的那个人,大概又老了一岁。于是,春天,在带来无尽生机的同时,又给人们带来一点春困,困顿于杨花似雪,困顿于云淡风轻,困顿于“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对于春天的描写从写实开始向写意过渡,从北宋郭熙的《早春图》和南宋马远的《山径春行图》两图,就可以看出端倪。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早春图》是幅巨制,纵158.3厘米,横108.1厘米,画左署款“早春,壬子郭熙笔”,作于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钤有“郭熙笔”长方印。这幅画给人的感觉是空山雨后,天气清新,山川滋润,万物生机盎然,笔墨间洋溢着喜悦的情绪。郭熙是北宋山水画名家,字淳夫,河南温县人。北宋神宗时为御画院艺学、待诏。其作品笔墨谨严,构图完整,写实状物都有必然的法度,于一笔一画间又将画家的胸怀情绪有度地表达了出来,非常符合中国文化厚重从容、怡然自得的文化品位,彰显了画家,乃至一个时代的文化自信、自尊、自强。所以,宋神宗很喜欢郭熙的画,将他的画在宫中到处悬挂。可惜,继位的宋徽宗不喜欢郭熙的画,藏之于库。从艺术史角度看,宋徽宗喜欢设色浓重、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彼时画风与郭熙时代大有不同。这跟宋徽宗在文化上打击元祐党人、绘画上推崇特定主题的创作、限制自由发挥有很大关系。比如他在《千里江山图》上说“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字里行间对文化的发展有一种上位者的权势气焰,十分明显和张扬。这种轻浮的神态与《早春图》表现的厚重空明大有不同。
马远的《山径春行图》描绘的是春天的江南,一名儒雅的文士,带着携琴的小童,漫步于春日山径,徜徉于柳色之间。一对黄莺婉转上下,野花芳菲,不沾衣袖,春野从容,得意忘怀。不惟画中人为春意所惑,读画人何尝不能从中体会出春天的生机呢?画面有南宋宁宗杨皇后的题诗:“触袖野花多自舞,避人幽鸟不成啼。”显然与画面本身的文化品位比较契合。野花自舞当时生机无限,幽鸟殷勤自是物我两忘。此图的柳树画法非常有味道,不惟画出柳色青青、柳条依依的感觉,更将柳树的旺盛生机表达了出来,以之体现春天的暖意和气息,当真卓有匠思。值得留意的是,这幅《山径春行图》是幅小作品,纵27.4厘米,横43.1厘米,大概也就一个平方尺左右,与将近六尺整幅的《早春图》相比较,一大一小,一实一虚,却都能将春天的气机表达得淋漓尽致。古人于绘画说过“技进乎道”,又有“得鱼忘筌”的说法,其实还是强调不能形式主义,不能本位主义,应“质以代兴,妍因俗易”,绘画当通过“美的形式”表达“美的情感”。如此而已,其他何必强求,又怎能强求?春天来了,绿草如茵,这是自然之理,若春天未到,以绿色染之,虽同是绿色,其实质相差何止于千万里!
宋人之后,中国画出现了文人画思潮。古人云:“反者道之动。”事实正是如此,在强调文人画之前,中国绘画似乎未曾缺少文人气,无论是顾恺之、吴道子、张萱、李公麟辈的人物画,还是王维、董源、巨然、范宽、李成、李唐、马远、夏圭、刘松年等人的作品,都显得神韵自足,文气盎然。反而是在强调了文人画之后,中国绘画开始走向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是写实的风格开始更加专注于写实,另一方面,写意的风格开始更加专注于写意。甚至,写意的画家看不起写实的作品,斥之为匠品;写实的画家最终也看不起写意的作品,以为不过是程式化的伪饰。这就等于两拨人去春游,一者过于注重自我感受,强调心情愉悦即春意所在,而忽略了欣赏自然之美;一者强调花开花在,自然变化与我等人类无关,拜服在自然美之下,岂不知笔墨之美实则远胜于客观之美。毕竟,春天不因人而有,春天之有无还有什么意义?董其昌的“南北宗说”实则只能被看作一个艺术史学习的方便法门,南宗北宗,其品位的高低最终还是要依赖于绘画本体的艺术水平,共同的文化脉络将使两类绘画形式殊途同归,承担着文化脉络的承续。
就此,我们下面比较的这组作品是元代高克恭的《春山欲雨图》和唐寅的《春山伴侣图》。
《春山欲雨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绢本墨笔,纵107厘米,横100厘米。作为元代的大画家,高克恭的出身比较特殊,他是色目人,社会地位比较高,但自幼接受的是儒家教育,所以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实践丝毫不比汉人差。在绘画层面,他继承了文人画的理念,参考学习了董源巨然的笔法,更直接学习宋代大小米氏家法,最终自成一家,对元代绘画的发展和完善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春山欲雨图》绘写江南一带山水,矾头皴法,笔触模糊,仿佛云雨淡抹。远山大小相对,云海苍茫,近山丘峦错落,树木葱茏,呈三角形排列,构图比较传统,师法董源无疑。至于其性情中的平淡天真,在远山的云雾间时隐时现,真是好一个春雨迷蒙的景致。
《春山伴侣图》同样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纸本墨笔,纵82厘米,横44厘米。唐寅富才气,但命运多舛,于是寄情山水,纵笔人生,笔墨跌宕起伏之间,温润醇厚的文化素养又充沛非常,真是妙笔生花,令人羡慕。唐寅又喜欢题诗,以书法之美,诗歌之韵,温润绘画因商品交易带来的挫折感,恰是此间种种纠葛,令画家情绪含蓄而热烈,千载之后,读画者依然能从中有所体会、有所感叹。此幅作品上,唐寅题诗曰:“春山伴侣两三人,担酒寻花不厌频。好是泉头池上石,软莎堪坐静无尘。”春天来了,两三好友入山寻春,处处寻春皆不可得,好在心有所好,既然觅春不得,莫若溪边大石之上,谈天论地,唾沫飞溅一如山泉泄玉,青山空明,宛若此心光明。画家品位高超如此,画面又空明清净,则何处不有春意?又何必处处寻觅?唐寅构思,真是天纵其资,以北宗手法,写南宗心绪,融合无间,浑然一体,非大才子,不能如此。难怪当年周臣说当让唐寅一头,因其腹中有千卷书在。
从构图上看,《春山伴侣图》也相当有想法。三丛树错落排列,然后又接着数丛树木偃仰呈s形,宛转而上,形成一个主线。然后人、屋安放,泉石错落,山路迂回,又是一条主线。之后是主山,虽然紧密却又井然有序,是第三条主线。三条线又纠缠在一起,丰富多姿,目不暇给。更可贵的是用笔十分干净,不啰嗦,以宋代山水画的骨骼,丰富元代文人画的血肉,顺势而为,不牵强造作,方硬峭厉之皴笔,柔化为婉转流畅之线条,笔锋峥嵘之处,略加水分就墨渲染。总之,画面笔秀温润,空明清净,韵致非凡,真是反映春天的中国画“神话”。
之所以用“神话”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绘画中的春天题材的作品,就是因为绘画中的春意生机往往并非自于画面的形式、色彩的艳丽,而是来自于笔墨的韵致,宛如春天万物的萌动,虽然细微,却强劲;虽然简单,却丰富多彩。唐寅少年得志,未尝不会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只是此心过于迫切,乃至欲速则不达,最后只能落魄江湖,所谓的“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其实掩盖的是未曾忘却的初心。有人说唐寅“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知所凭何据?我倒是觉得他心乱所以寄情山水以求平静,情困所以聊到江湖以求远离。于情于心,他都没能彻底遗忘,总是和这个与他格格不入的世界有羁绊,不忘初心,不悖初心,这才是唐寅所以伟大之处。首先,他的审美价值观非常正统,没有因为命运的蹉跎就妄自菲薄、怨天尤人,其次是他用笔取疾势,绝无躁动之嫌。清大画家恽寿平评唐寅的画:“远攻李唐,足任偏师。近交沈周,可当半席。”这是说他虽然师承南宋院体,但其笔致圆转灵逸,不露圭角,可与沈周的温厚从容相媲美。依我看来,还是唐寅在审美价值观上与沈周保持着一致有关。正如我们对春天的感觉若相同,则无论以何种语言,以何种文艺方式,表达的结果应当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先前一直在讲春天里的古代中国画,将其脉络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主线,是因为我们希望落脚的审美观的统一问题,我们举例都是沿着两条主线能殊途同归的思路寻找,并没有将那些将两条主线极端化的作品收入,尤其是写实风格的作品,比如郎世宁的《二月踏青》,任熊的《万横香雪》,还有诸多花鸟画家的花卉作品,比如石涛的《桃花》,恽寿平的《富贵牡丹》等等。这是因为我们相信“神话”作为一个主题,它总是需要取舍,或者以幻修真,或者信以为真。总之,“学而时习之”需要的是“不亦乐乎”的真诚,艺术需要美,美包含真诚和善良。以此来审视一种“神话”的继承和发展,结论才有意义和价值。否则,缘木求鱼,舍本逐末,总非艺术鉴赏的正道。出世和入世,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两者在动机目的上绝对不矛盾,这就是中国画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所在。
清代恽寿平有一幅描写春天的作品,名为《春云出岫图》,纸本设色,纵129厘米,横49厘米,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此幅作品拟高克恭的笔法,以米氏皴法为之,清秀温润,有蔼然君子之风。这幅画需要介绍的是它的题跋。其曰:春云出岫,拟高尚书法。这是点明绘画本源,师法高克恭。不过,在后面的题跋中,他又写道:“……在南岳山庄观铜笔峰云起得此意。”也就是说,他先看到现实自然中的春云出岫,才有师法高克恭的艺术实践,究竟是以高克恭的笔法印证自然界之春云,还是以之反证高克恭的笔法,其实不必追究。作为鉴赏者,我们需要的是与画家共情,甚至借助于画家的作品,将我们的情感升华到画家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境界。这才是真正的“神话”传承。恽寿平说过:“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所谓的“情”,就是流露真诚的情绪,而非欲望和贪念。诚者明也,自诚若神,于鉴赏来说,即回归本心,则知绘画之好坏,原在一念之间,根本无关名利地位、价格高低。这当然不是“神话”,而是客观的事实。
可惜,无论是“夜静空山”式的清净自如,还是“万紫千红”式的热闹舒畅,春天在我们心里总是很容易掠过。我们要么伏案工作,浑然忘记花开花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要么热烈地附会春花灿烂,搅动心绪,忘记初心。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关注“春天里的火车”,却总是没能如愿前往。不过,我没觉得有什么可遗憾的,毕竟,在案头心中,中国画的春天一直如“神话”般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