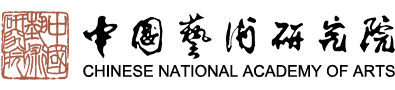张振涛《音流滚滚——七千小时录音与“世界的记忆”》
时间:2022-07-12 来源:“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微信公众号
没有文字的历史,是口传的历史;有了文字的历史,是平面的历史;有了录音的历史,才是多维的历史,而对于音乐史来讲,这样的历史才算完整。可以说,完整的音乐史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的。作为音乐家,杨荫浏、李元庆赶上了这样的时代,所以也做出了前人做不出来的“掷地有声”的业绩。习惯于按下放音键回放音乐的当代人,只能约略体会刚刚听到录音的音乐家伴随20世纪来临时的欣喜,终于可以把喜欢的声音录制下来一遍一遍、循环往复地回放了,对于渴望把心里蹦出来的、嘴里唱出来的、手里弹出来的、耳朵眼儿听到的美好旋律永远记下来的音乐家,乐不可支,喜不自胜。录音技术的发明是音乐世界中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对于听觉艺术来讲,就是建立了音乐成为完整意义上的音乐的基点,就是托载从业者找回声源的扬帆巨舟。录音技术打破了记录历史的载体和工具主要靠文字的单一途径,把字母字、图形字、方块字以及一切平面符号不能记录却勉为其难、越俎代庖的信息收录下来,让嘲笑音乐史是“哑巴史”的讥讽,留在了寂静的历史中。一部吟咏叹赞、吹拉弹唱的历史,开始成为音乐家的历史。听觉系统第一次在表述历史的领域派上用场,热热闹闹的动静,有声有色地挤进了历史档案。
录音机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那便是音响资料以史无前例、昂首阔步的姿态,涌入了记录历史的行列。为音乐家进入历史,堂而皇之地注册,使音乐家成为有资格守护历史并为真实而辩护的大嗓门巨人。当代人终于认识到“视听遗产”对历史学的意义。这是“寻声暗问弹者谁”的解疑的技术保障。录音机留下了民间艺人抹不掉的高歌游吟。对于音乐家来说,录音机的按键才是真正让灵魂快乐到出窍的键钮。
一、“世界的记忆”
199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无意间将收集的音响资料情况,报告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想,对方立即派来了专家。1997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七千小时的录音资料以“世界的记忆”项目(1992年设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注册的“音档保护单位”。教科文组织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颁发一张证书,直到音乐研究所提出要求,秘书处才意识到应该颁发一张荣誉证书。2001年3月12日,音乐研究所办公室的夏铭竹,到文化部取回了巴黎转来的证书。时任所长的乔建中让我到东直门外新源里冲洗照片的小铺,花五十元钱做了一块今天看起来相当粗糙的金黄色铜牌子(当时还有人觉得浪费)。写下这件小事是因为它可以反映了当年的经济状况。和今天的大手大脚比起来,实在觉得寒碜了自己的“招牌”。不管怎么说,标有教科文组织标志的《世界的记忆》证书,转换成一块铜制的金灿灿的牌子,挂到了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的大门口。
当时不知道自己做的事到底符不符合国际标准,有没有学术价值,值不值得骄傲。不了解海外同行怎样收集、怎样保存以及怎样评价中国人的工作。奥地利音响档案馆馆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音响专家舒勒博士(Dietrich Schüller)来到这里。面对人家的音像档案史,我们免不了底气不足。
一个奥地利音响档案馆的馆长舒勒,一个中国音乐研究所的所长乔建中,客客气气,面对面坐了下来。客人渴望了解中国人在过去50年间干了些什么,主人渴望了解外国人对过去50年干的事怎样评价。两位年龄相仿的男人,都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不用探寻职业深度,一两句话就知道对方的积累。对话背后,彼此仰仗的是专业机构、采访阅历和只有音乐家才有的直觉。这些背景汇聚起来就是那场“奏鸣曲”的主部主题。宾主寒暄,聊了几句就投缘了,一拍即合,相谈甚欢。
舒勒边走边看,时而抽出一两卷录音带,时而抽出一两张胶木唱片,弹弹尘土,靠近窗户,对着阳光,眯起眼睛,仔细打量,估摸着状况,时不时提一两个问题。从重得像块铁疙瘩的钢丝录音带,到大多数人没见过的滚筒录音带,再到各种开盘录音带,以及盒带、金属带,他都一一过目,随手抽取几盘录音带和几张唱片,到录音机和唱机上播放听检。最后,走出图书馆,表达了由衷地赞叹。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外国专家的评价,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原来杨荫浏团队所做的事,是全世界上的最大盘子!世界不多几家音响收藏馆,没有像中国音乐家一样收集过如此海量的传统音乐,甚至有着相同文化政策的前苏联、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如此大面积收集过。舒勒说,印度、埃及历史悠久,音乐不比中国少,但文化机构没能像中国人一样有所作为。
有历史是一回事,收集历史是另一回事。中国不但有历史,还善于收集历史。这一点过去如此,现在还如此。杨荫浏、李元庆之所以能够做出经天纬地的业绩的原因,就在于此。这大概就是印度、埃及为什么没有像中国音乐家一样积累起惊天财富的原因。传统让中国人永远这样行事!如此行事,中国觉得普通,反倒让外国人一总结,才觉得自己的“下意识”如此超前,如此不起了。
人类记录自己声音、把无声历史变为有声历史的第一批录音载体上,留下了中国人的声音。因为从纸面介质向音频介质记录历史的转折点上,站着杨荫浏!
他几乎是在无人要求、无人催促的情况下,出于职业敏感,出于历史意识,自觉启动了这项工作。有件事对他具有震动性。1947年,驻上海的瑞士领事馆希望中国音乐家提供一些传统音乐的乐谱和音响资料,当时,没有一个组织和音乐家可以拿出乐谱和音响资料(即使外国唱片公司录制了一些质量驳杂的戏曲唱片)。中国人拿不出自己的音乐来!杨荫浏在杂文《旧乐收集与出版漫谈》(1947),记录了尴尬与屈辱的感受。
所以烽烟俱净、新的社会环境提供条件时,他立马开始录音,进展神速,神速到数十年后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的程度。他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文化部提供了外汇紧张的情况下刚刚进口的钢丝录音设备,传统音乐尚未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干扰,原汁原味,原生原态,刚刚翻身解放、扬眉吐气的民间艺人,坐在那里等他到来,愿意把准备了一辈子、积攒了一肚子的经典提供给他。只要走进田野,俯拾即是,遍地珠宝。只要有录音机,不几年就能“粮满仓”。这可不是随便哪个国度都有的。
舒勒热情洋溢地赞美“收藏丰富”“技术合格”之前,谁也不知道这堆不怎么被自己高看一眼的音响档案价值几何?现在,知道人家在做什么了,人家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舒勒的评价,让我们立马高攀了已有百年历史的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建于1899)和德国音响档案馆(建于1900)以及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等老牌音乐资料馆。几家以收藏音响资料为使命的机构,相隔千山万水,居然因为音响档案迎头碰在一起。前者的举荐竟然让后者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家单位,一转眼到了联合国教科文不给中国政府打招呼就批准了获奖单位并因此设立了一项特殊奖励的层面,音乐研究所的音响收集居然一下子与两家欧洲“百年老店”齐头比肩!以技术为荣的西方骄傲,戛然停止在中国音响档案馆的大门口,戛然停止在1997年。
五十年斗转星移,中国学者的田野成果终于开出了花,长期徘徊在现代边缘的音乐学界,真正尝到了先天之下、立于风头的甜果,跻身国际音档收藏、雄居世界前列的身躯,竟然出现在音响界。传说的宝藏真的演变为震惊世界的事,一并让团队获得了国际关注。七千小时录音像“化蝶”一样变成金子,丑小鸭一夜间成天鹅,家乡土鸡一夜间成凤凰,如同童话中虚拟世界的升迁。从不自信到自豪,巨大反差让人恍若隔世。无须说,涅槃的感觉超级不错!
我们不能不佩服杨荫浏、李元庆的学术建设意识,不能不回过头来反观两位先行者的远见卓识。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三大宝藏,乐器收藏、音响收藏、图书收藏,样样响当当,个个不含糊。这个格局包括了一个研究机构应该具备的所有资料,外人对此羡慕不已。他们何以总是超前一步?按理说,杨荫浏、李元庆也属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想所干的事不会超越其他人。然而,他们的确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他们有一种“大家”才有的本能洞察力,一种体现和还原真实的叙事力。从一个时代过分吵闹的声音中,屏住呼吸,平心静气,听辨民间真声,守护历史原貌。实在说来,这个本事,就是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朴素感情,体会起来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世界的记忆”的荣誉称号,是对已经听不到赞美的前辈的追赠。七千小时,一份多么长的时量,每一分钟都意味着一群寻遍穷乡僻壤、山寨村庄的采录者七十小时、七百小时的路程!七千小时就意味着“八千里路云和月”!
二、第一部音响资料工具书
七千小时的录音是什么?一本工具书记录了全部内容,那本书目录上的每一行标题,都连接着像民歌海洋一样的巨量内容。1994年,音乐研究所编辑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录音磁带部分)出版,在时任所长黄翔鹏、副所长乔建中建议下,资料室全体人员集体参与了编辑。以李久玲、范俊英、李兵为代表的馆员,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为汇集唯一一本音乐学意义上的音响目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把一柜子一柜子的卡片,分门别类,查照排序,变成一行行目录。他们心中的关键词,当然与记录的内容一样:留住历史。
工具书的价值却不仅限于音乐研究所。录音者可能未像拉开距离的后人一样意识到音响资料的价值,后来者把名目著录成编,呈现流水账般的细目时,大概也不能意识到其中价值,只是到了需要考虑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再也不是无声历史而是一部弹着、吹着、唱着、吟着的历史,才能慢慢品味原来整整齐齐码在书架上、现在整整齐齐码在目录上的音响资料的价值。目录出版后又过了十几年,人们才能更深地解读工具书的意义。面对她,大概没人敢夸耀自己听到的一方之音最精彩了,因为音响档案中的音乐是最精彩的,因为那里集中了全部的精彩。
每一条资料的信息包括:曲目、体裁、民族、流行地、表演形式、作者、表演者、节目来源、所藏号等。磁带形式由四种标志给予标识。翻看目录,基本可以了解版本、年代。从音乐学角度说,只有音响本身,就等于切断了与田野现场的关联,一盘录音如果不配以文字信息,就等于户口上只有人名而没有年龄、性别、籍贯,那等于黑户。音乐学的录音不但要有声音,还要有文字;不但要有被访人的声音,还要有被访人的姓名、年龄、性别、民族、地点、时间、场合、所用乐器及其组合等信息。这才是学术意义上的录音资料。声音文本,相互参照,前台后幕,一一对应,才能帮助研究者感知现场。一般录音既无文字著录,也无背景出处。有了配套意识,音乐学的录音就有了另一番景象。提供背景,让人亲临现场,才能使历史解读成为可能。文字音响,相辅相成,就是最低限度的组合成本,最高限度的学术活力。
音乐研究所的音响资料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录音制品,就在于配备了相关信息,因而身价倍增。录音大部分来自专业研究人员从1950—1996年经过46个年头遍布全国的考察搜集,其中也有邀请民间艺人到北京的录音,来自各地音乐机构或组织以及个人的馈赠,还有不同地方广播电台或广播站的转录。
杨荫浏和李元庆亲手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收藏民族宝藏的理想,使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技术人员与他们一样长时间保持了同步的学术意识,这种意识带来了一批快马加鞭的累累硕果和学科理念催生的音响。爆炸式递增,是这批人没日没夜、一点一滴、滚雪球般积累起来的。掐指算来,这支队伍的成员当年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干出这番经天纬地大事的人竟然那么年轻,与其干成的事业分量比起来似乎太年轻了,年轻得让人不敢相信。以往的年轻人闷在家里干点不起眼的事,聚到一起,跟着李元庆和杨荫浏,竟然爆发出了排山倒海的能量,把千山万水之外的录音全部划拉到怀中。他们一手建立起来音响资料馆,让七千小时的分量压在轻飘飘的音响历史的开篇。
三、音流滚滚
如果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图书馆有图书、乐谱、唱本等藏品可与一般图书馆的概念对号入座的话,录音储藏则是另一片全然不同的绿洲,也是国家收藏史中最晚添进来的神话之一。位列全国之冠的音乐档案棺,把飘浮在神州大地的滚滚音流聚拢一起,汇成一股冲天巨响。在李元庆、杨荫浏带领下,一班人马把个“鼓全锣不全”的图书馆配套成龙,揽了一桩即使有金刚钻儿也没人敢揽的“瓷器活”。如果不听音响,谁也不敢相信,凭着几台老掉牙的机器就把偌大一个国家中几乎所有民间音乐的品种收集齐全。好在,那个建立神话的时代出现的神话是一摞摞的,解释起来顺理成章,比起把贫油的国土挖出石油、比起把天堑化为通途、比起把小米加步枪换为氢弹、原子弹,这点事似乎算不得什么,但对于音乐界,这个库藏放射的能量,确实如同原子弹!
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80、90年代,所有愿意伏身民间的中国音乐学家、作曲家、表演艺术家,都曾到音乐研究所的图书馆聆听过田野吹来的“国风”。著名作曲家朱践耳、李焕之、吴祖强,音乐学家汪毓和、戴鹏海、陈聆群,表演艺术家毛阿敏、关牧村、姜嘉锵等。音乐家们带着一副痴迷神情,眯着眼睛,目光悠远,好像迷失于田野上的孩子。参观者无不偏爱听一听老唱机播放的出版于一百年前的老唱片。风靡世界的简便录音机虽比手摇唱片机用起来方便,但对于老派音乐家来说,那可不是随着唱片转速的减弱而飘忽不定、吱吱啦啦的音响,而是一段流淌着怀旧诗情的岁月,正是因为要手把摇杆、上紧发条的过程,才增添了自我加工的迷醉感。许多音乐家喜欢一边跟收藏者聊着关于这段录音来自哪里的问题,一边守在录音机边,听着按原速转录中压得很低的音响,迷迷瞪瞪地感受民歌的浓艾苦香。此时此刻,即使是一首普通民歌,都会有阅读两千年前《诗经》、一千年前《竹枝词》、一百年前《挂枝儿》的浪漫错觉。
作为收藏领域最柔软最无形的地带,音乐图书馆瞄准的是一切与声音有关的“风语”。录音彻底改变了人们闭耳塞听的经验和只用眼睛吸纳信息的渠道,打开了一个让人进入“曲馆、剧场”,见到大师、巨匠,亲耳聆听、仰慕已久的“真人版”的愿望。想想吧,你能听到聂耳自己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你能听到阿炳自己演奏的《二泉映月》,你能听到梅兰芳自己演唱的《贵妃醉酒》,你能听到色拉西自己演奏的马头琴《天上的风》,那是啥感觉、啥滋味呀?虽然有经过降噪、拼接、混响、修饰一新的音像制品,历史主义的本真却永远会在音乐家心底涌动,因为他们对音乐艺术自有一番不同于店铺音响的独特理解。
音响设备与学术研究结合催生出了一个学科。一个刚刚开始有理念却没手段的学科,遇到了科学技术的强大帮手,处于边缘的“受气包”一下子被扶到了学术大堂的中心,毫不客气地把许多古老学科挤到一边。这个学科就是30年前的“民族民间音乐”,今天的“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运气真好!利用迅速积累资料的机器,把新生变成老成,把锐气变为城府,把英姿勃发变为羽扇纶巾。相比而言,由西方无数高产作曲家联合起来、集体行动、日积月累的作品集——几乎可以称得上全世界增长最快、汗牛充栋的乐谱集,在民间音乐采访积累的乐谱集面前,一下子就变矮了。谁敢在五大《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面前“摆谱”呀!机器的速度,超越了所有专业作曲家的速度!民间和历史的强大,借着录音机的转速,瞬间变成巨人,达到只有流星才能达到的速度。一个巨人式的学科一蹴而就,一举成名,它一张嘴,就响彻云霄,盖倒了所有声音,让艺术门类的其他学科带着酸溜溜的腔调在民族音乐学家面前表达出高度嫉妒背后隐藏的高度羡慕。录音机让一个古老学科在最短时间完成了现代学科必要的资料积累,数千小时连接起来的“长城”,使任何一个学科都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后人带着敬佩之情称颂杨荫浏改写“哑巴音乐史”的说法,不仅是指文本加进的大量谱例,而且是以他亲手收集的大量音响为支点。录音机帮助一个学科从坐而论道到深入田野,彻底转变了运作方式,改写了几千年的规则。
后人不无羡慕地认为,杨荫浏和李元庆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如同比尔·盖茨、乔布斯在计算机世界获得的空间力度,“音响资料馆”是他们凭靠文化自觉在国家初创期向世界展示的一份保护传统的完美答卷。后人可以举全国之力兴建一个音乐博物馆,但人们更希望在博物馆里祭奠创意者的远见卓识,同时将文化自觉等关键词串联而成的意念一并装载,待后来者思考“其命维新”的古国怎样在一次次健全机体、一次次完善收藏中激活了一个古老学科。传说中第一代已经一个个谢幕,复归长河,他们在短短十几年间完成了从一无所有到学科齐备的跨越,支持其跨越和支撑其力量的就是理想主义和文化自觉。乐器博物馆、音响档案馆、音乐图书馆三足鼎立的定位,被一点点确立、一步步实施、一圈圈扩展,这个历程就是第一代创始者把蓝图升华为档案的过程。理想主义是那个时代文化人的人生态度和共性,它成就了20世纪育木成林“百鸟朝凤”的音响收藏。毋庸置疑,杨荫浏、李元庆是一对用声音这个看起来不存在的存在证实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学科引航者。
(本文原载《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1期,转载于《杨荫浏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
作者

张振涛(1955—),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特聘教授。著有:《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声漫山门——陕北民族音乐志》,论文集:《诸野求乐录》《风声入耳》《燃烧的琴弦》《响鼓重槌》《冀中学案》,主编《杨荫浏全集》(十三卷)、《黄翔鹏文存》(上下卷)、《中国工尺谱集成》(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