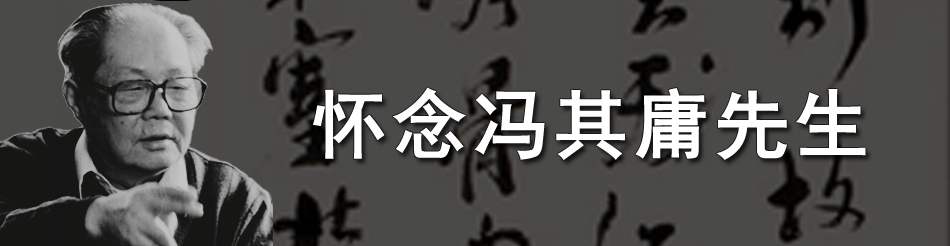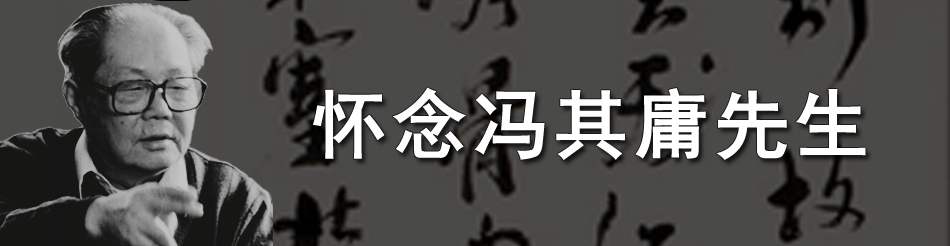风雨长途 笔底乾坤
---追思冯其庸先生
今天中午,先生已远行。此文是先生生前所嘱的最后一件事。现略加改削,以为纪念。
放在时空的坐标上,冯其庸先生以九十四岁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长途,以“行走天地间”遍历名山大川涉险求真的坚实脚印,造就了一个文化学术的传奇。仅有时空两个维度还不够,最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意志力和创造力。冯先生以三十三卷逾千万字的著述和量多质优的书法绘画及摄影作品,收乾坤于笔底,气象万千。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全景式的冯其庸,丰富、正大、雄奇。
一
冯其庸是学问家、艺术家、旅行家,却又不止于此,三者往往是叠合的、交叉的,分割开来就失去了冯其庸。难怪人们觉得概括冯其庸的成就是个难题,哪个称号对他都不尽合适、容纳不下。究其实,是因为他具有大视野,常常跨学科。
他从江南农村走来,到县城,以后到了首都北京。三十出头就在大学里独立承担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从先秦一直贯通到明清,编注了《历代文选》和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义,受到好评。但他不是一个书斋式的学者,不仅在书本上熟悉那些优秀的作家作品,而且要实地印证和亲近。他到过湖北秭归的屈原故里、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墓,拍摄过陶渊明时代的墓砖、凭吊过李白捞月的安徽采石矶、杜甫出生的河南巩县窑洞,更寻踪白居易写《长恨歌》的陕西周至游仙寺和山东章丘的李清照故宅漱玉泉。晚年到海南更着意寻访苏东坡谪贬来此的遗迹故地,九十三岁还为海南东坡书院题了“儋阳楼”的匾。冯先生是教师、教授,但他绝不是侷守三尺讲台的教书匠,而是引导学生去读天地间的大书。他曾带领研究生外出学术调查,历时两月,行经鲁豫苏皖川陕等七省近三十个县市,览江山胜景,觅历史遗迹,参观博物馆,更留意出土文物和碑碣石刻。使学生眼界大开,受益无穷。总之是要把书读活。这里还可举一个具体例子,他在江西干校时一次找辛弃疾的墓地未果,却意外发现这地方的山都是倾斜的,像万马奔腾一样往前奔跑,辛词中“青山欲与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的句子是得自这里山的气势,不是原先读词认为是诗人的想象。类此情形很多,无论读史记、读杜诗或其他作品,都可在实地得到印证和深化。
他说,“我是不管到哪里,都能跟做学问联系起来的”。“学问”是有生命有温度的。
先生的视线还超越了文学,直穿到远古,对原始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去陕西“四清”时,工作之余在长安县王曲地区发现了原始陶器的碎片,以后写成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经过和文化遗存状况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专业的《考古》杂志上。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和钻研持久而深入。文革中,他还抢救了多件有价值的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他对于全国各地新的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一直十分关注,尽可能地亲自前往察看。在广泛实地考察和综合研判的基础上,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元论不符合实际,应当是多元的,不仅有夏商文化、秦晋文化,还有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西蜀文化,都应属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这样的见解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实地考查还能纠正书本的失误,不论是外国学者的著作还是中国古籍都要接受事实的检验。当他七赴新疆时,至克孜尔石窟,翻越绝少人去的后山,寻找207窟即“画家洞”,几乎无路可走,只能在危岩绝壁上攀行,到达后仔细辨认壁画,感到日本学者羽田亨所著《西域文明史概论》所言不确,壁画所绘作画者不是武士是画工,腰间所悬的是笔盒而不是短剑,服饰发式的西化反映的正是古代吐火罗族的画工。十赴新疆穿越罗布泊到达龙城,此为典型的雅丹地貌,而《水经注》把龙城记为“胡之大国”是误解。类此,都见出冯先生不畏艰险,信服实证,追求真知的精神。
可见先生不仅治中国文学史,还治中国文化史。不止于此,人们知道他对汉画像深有研究,提出过汉画像是“敦煌以前的敦煌”,是中国艺术未受到外来佛教影响前的本真形态,这就是艺术史的课题了。我们难以一一认知先生所涉足而且深入的领域,但他的大视野、跨学科也由此可见一斑。
二
识其大,方能论其专;翻转来,专学的精深,得益于大的依托。红学之于冯其庸,应作如是观。
冯先生以红学名世,他的诸多称谓中,红学家是人们最熟悉的。可以从下述方面来看他的红学贡献。
首先是以一系列的著述确立了他的学术地位。这里先要回溯一件轶事也几乎是个奇迹。“文革”初期,痛心于造反派抄走了家中的《红楼梦》,他在人身不自由、常被批斗、两派武斗的高潮中,于夜深人静之际,冒险秘密抄录了借得的庚辰本石头记,全书连正文带批语七十万字,全部用毛笔小楷精抄,历时七个月完成。此举恐怕是空前绝后的文化行为,出于先生对《红楼梦》的珍爱。冯抄本在今天也就成为一件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文献,成为珍贵版本和书法艺术的双壁。
为了知人论世,弄清曹雪芹的家世和籍贯,先生在深研谱牒、广稽文献、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论证了雪芹父祖的籍贯应为辽阳。此书经几度充实修订再版,一直出到第四版。同时,他对石头记的早期版本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先有《论庚辰本》的发表,以后又及于他本,汇集成了《石头记脂本研究》一书。还有一本较早由香港三联出的《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全由先生亲录,其中许多旧址今已不存,十分珍贵。这方面的成果,充分体现了他富于实证精神和文献功底的治学特色。
然而先生并不满足于此,他对红楼梦的文学本体、思想意蕴、艺术创造同样下了很大功夫。除了《千古文章未尽才》等重要论文外,新世纪以来还有《论红楼梦思想》、《红楼梦概论》(合著)两种著作。此后,更用五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一百六十多万字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此著有丰厚的学术含量,将自身和学界最重要的成果加以吸纳,从家世背景、历史文化、以至艺术结构、遣词用字各个方面尽力涵括,可称是曹红之学的集成之著。
其次,是以组织家和带头人的身份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红学。
如果要谈论新时期的红学,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冯其庸。这不仅因为在新时期之初,他会同学界前辈和同辈倡导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成为继吴组缃先生之后的第二任会长,还因为同时创办了《红楼梦学刊》和组建了红楼梦研究所。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实施和完成了一系列红学基础工程,如《红楼梦》的新校本、汇校本、汇评本、大辞典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以脂本为底本的新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至今发行已超过500万套,拥有广大的读者。在这过程中带动和培养了一批红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此类基础工作其影响深远,当非个人著述所能比拟。在此期间,无论是俄藏本的洽谈,还是甲戌本的回归,都经先生参与鉴定;更不必说历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和海内外的讲学,都有先生的主导、参与、支持、身体力行。
红学是显学,是一个令世人趋之若鹜又避之不迭的领域,这里充满了争论、充满了挑战,各种问题少有定于一尊的结论,却有著书立说的空间。要在这一领域立足进而领航不是件容易的事,冯其庸以其广阔厚实的学术功底进入这一领域,并非要一统红学天下,而是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著述卓然成家。许多见解得到认同和呼应,而某些主张引起争论甚至反对亦不足为奇。如墓石,先生坚信不疑而学界有不同甚至否定意见。为此,先生编有墓石研究的“论争集”。在红学界,这似乎是一种常态,争论不断,也从某个方面彰显着活力。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红学远较过往多元多维,呈现繁荣景象。冯先生所引领的曹红之学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大红学”吧。
再次,不能不提到冯其庸的多才多艺博闻广识对红学的滋养和渗透了。私见以为治红者在知识结构、艺术修养、生活阅历诸多方面愈能追踪作家作品,则愈有望进入治红佳境。冯先生的阅历修养显然具有天然的优势。这里只能略说一二:先生能吟咏、擅书法、喜绘画、精戏剧、好交友,识鉴文物,雅好收藏。手边文房四宝,均有来历,习惯用徽墨、湖笔、乾隆纸,曾得奇石凿砚,撰砚铭。往昔善饮,醉后作书画,竟臻上乘;精于茶事,种茶、炒茶、品茶,了然于胸。他对园林泉石、陶瓷紫砂,均有卓识;还懂家具制作,肴馔烹调。别忘了,冯先生指导的扬州红楼宴十分地道、名扬中外。
要之,红学和由此衍生的红楼文化,面宽水深,宜乎先生涵泳其中。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红学之舟的领航人。
三
最令人震撼也最难企及的当数十赴西域,探得玄奘取经之路。从1986到2005的二十年间,冯先生十次去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登上喀喇昆仑山颠,寻瓦罕古道,穿越人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访楼兰古城,先生在古丝绸之路和取经之路上颠簸行进,绝尝艰辛,终于考得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并在明铁盖达坂山口树碑为纪。这是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的玄奘行踪考察成果,它震惊了佛学界、敦煌学界以至整个文化学术界,中国佛教学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闻知惊喜振奋,在医院专门写信给冯先生称赞“考实周详”“功德无量”。
学界友人谓先生西行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以年逾古稀的高龄且有心脏疾病,在高原缺氧的条件下,涉流沙、登冰峰,上达4900米的世界屋脊红其拉甫国境线,下至海平面以下154米的吐鲁番艾丁湖。在荒漠之中野营七日,感受天地之大、星月之明。不仅纪录于文字,还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这在现当代中外学者中,恐怕没有第二人。
先生的西行,大多是在退休之后。他还提出了极富战略眼光的创立西域研究所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我以为西部学的实践和倡议是冯先生晚年即近二十年生命放出的异彩,犹如一道绚丽的晚霞。人道夕阳无限好,先生的夕阳何其壮丽,可与朝阳同辉。冯其庸西域学的开拓性贡献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先生为自己的口述自传题名“风雨平生”,“风雨”二字十分确切、意味深长。童少年经历过日寇入侵的腥风血雨,正当盛年又遭遇了“文革”的疾风暴雨。这是言其大者,生死攸关;余者明枪暗箭、大坎小坷,如影随形。然而,先生从未灰心丧志,没有丝毫懈怠,历经风雨淬锻,为人为学更加纯粹、更臻成熟。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冯先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那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神圣的东西,就是对生养自己的祖国母亲、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沉挚爱和坚强信心。战乱、饥饿、失学使他投向革命、渴求知识;“文革”逆境中他独立乱流,默诵《正气歌》自励;别人卖书他买书,坚信文化不会灭绝。
传统文化之于冯其庸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这点十分突出。在他的心目中,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岳飞、文天祥等等一系列优秀人物,是他崇敬的对象,也是力量的源泉,不仅从书本上认识他们,也从实地去亲近他们。唐玄奘更是他自幼心慕的偶像,不辞万难的玄奘精神,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西行的征程,照亮了他的人生。
对中华文化的坚强信念即文化自信,为冯先生终生恪守,亦足资后学永远追随。
在此,不计工拙,谨以如下联语敬挽:
红学无涯,玄奘作灯,魂归大荒青埂下;
黄沙万里,冰峰凭眺,一笑扬鞭夕照中。
(注:下联嵌入先生诗句)
二0一七年一月廿二日先生逝世后七小时
附照片3张,是2016年11月17日在冯其庸先生家中拍摄的,也是和先生最后见面时的照片。



|